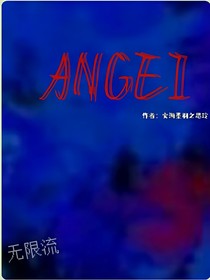纸坊的灰烬 (2-1)
沈砚之捏着那截钢笔走出档案室时,檐角的雨珠正顺着瓦当滴落,在青石板上砸出细小的坑——那坑的形状,竟和黑木盒底的刻痕重合。他想起李建国纸条上的“墨砂掺铅”,忽然明白赵德发的死因:铅中毒会导致嘴唇发绀,而那银灰色粉末,正是未经提纯的铅砂。
“纸坊在哪?”他转头问李雪,她正用袖口擦拭档案柜上的墨痕,暗红色的印记在柜面晕开,像朵绽开的血花。
“在镇西头的河滩边,”李雪的声音发飘,“我爸以前常去那,说纸坊的桑皮纸能存百年字迹。”
纸坊的木门挂着把锈锁,锁孔里卡着半片桑皮纸,纸上的墨砂还没干透。沈砚之用钢笔撬开锁,门轴发出“咯吱”声,惊起梁上的蝙蝠,翅膀扫过积灰的竹帘,露出墙上的字:“以砂为证,以纸为凭”。字迹遒劲,是李建国的笔体。
作坊里堆着成摞的桑皮纸,纸堆旁有个石臼,臼里的墨砂泛着金属光泽,铅含量远超正常标准。石臼边缘沾着些纤维,和赵德发砚台边的植物绒毛一致——那是文竹的根须。
“文竹能吸收铅砂,”沈砚之捻起根绒毛,忽然想起书房窗台上的花盆,“有人用文竹来养毒。”
墙角的灶膛还留着余温,灰烬里混着些未烧尽的纸,纸上的字迹被火烤得发黑,却能辨认出“五十万”“赵德发”等字样。他用镊子夹起一片残纸,发现纸的边缘有个月牙形的缺口,和老陈鞋后跟的碎纸缺口完全吻合。
“老陈说纸坊老板十年前就走了,”沈砚之对着光看残纸,纸纤维里嵌着几粒铁砂,“可这灶膛的灰,是昨夜烧的。”
作坊后院有口井,井绳上的水渍还没干,井壁上缠着圈红绳,绳结和多宝阁钥匙串上的一样。沈砚之放下水桶,桶底沉着块碎瓷片,瓷片上的兰花图案,正是书房钥匙柄上的花纹。
“这口井通着镇外的河,”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门口传来,纸坊老板拄着拐杖站在雨里,他的蓑衣沾着墨砂,“十年前,李副镇长就是从这把账册运出去的。”
老板说,当年李建国发现赵德发挪用公款,怕账册被毁,偷偷藏在纸坊的桑皮纸里,用掺铅的墨砂做标记。“赵德发找了三个月,最后放了吧火,说是纸坊走水,其实是想烧账册。”
沈砚之突然想起书房窗玻璃上的针孔,孔周围的乌痕是铅被高温灼烧的痕迹——有人用针管从外面往屋里吹铅砂,而赵德发手指的伤口,正是接触铅砂的入口。
“昨夜你在这?”
老板指了指灶膛:“我回来取些旧纸,看见李雪往井里扔东西,是个黑木盒,和当年李副镇长藏账册的盒子一模一样。”
沈砚之的心猛地一沉。他冲出纸坊,往镇长宅邸跑,雨幕中,老宅的轮廓像只蛰伏的兽。推开书房门时,老陈正蹲在文竹旁,手里拿着把小铲,花盆里的土被翻得乱七八糟,半截钢笔躺在土堆上,笔帽上的兰花缺角处,沾着新鲜的根须。
“你在找什么?”
老陈手一抖,铲子掉在地上:“我……我想把这晦气的花扔了,当年李副镇长就是用这花……”
“用这花养铅砂,”沈砚之接过铲子,铲尖挑起块碎纸,纸上有老陈的指纹,“十年前你帮赵德发烧了纸坊,昨夜又帮他藏了账册,对吗?”
老陈的脸瞬间垮了,像被雨水泡烂的纸:“他说只要我帮他,就把欠我的工钱还了……可他没说会死人啊。”
窗外的雨又大了,打在《寒江独钓图》上,把画里的孤舟泡得发胀。沈砚之盯着画框的磨损处,那里的漆下露出一行字:“雪藏此画,待铅砂尽”。是李建国的笔迹。
纸间魅影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无限流1ANGEL
- 双男主,无限流,原创
- 0.7万字6个月前
- 雷声
- 个人经历改编,风格比较神经,每章会比较短连载ing,不一定什么时候更新(别打我)意识流小说,因为本人是同志,所以主角也是同志,不喜勿入文刀十......
- 2.8万字6个月前
- 诡异复苏:我的爷爷是万鬼之王
- 爷爷的葬礼上,我得知惊天秘密,遗产中的小本子,记录着被所有诡异疯抢的秘籍,一个小小的上班族,竟然是万鬼之王的后代,在重重迷雾中,我在寻找爷爷......
- 5.7万字5个月前
- 七国之主
- 嬴政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朝代,在这里,七国争霸,嬴政听到这消息之后没有害怕,反而大笑道,如此江山,方才有趣,等朕统一天下,其......
- 1.0万字3周前
- 转眼间的十八年
- 零碎的生活,不完美的自己。
- 1.5万字3周前
- 神印劫
- 天地是生命编织的棋局,每个生灵诞生时,灵魂深处便烙下一枚“神印”——有人因它掌控元素洪流,有人却被拖入永夜疯癫。千年间,众生对神印既敬畏又恐......
- 5.3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