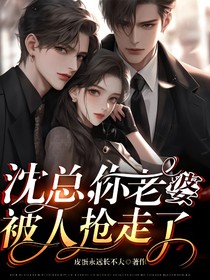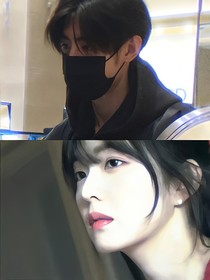枫红与叠影 (2-1)
霜降的风卷着枫叶,给回春巷的青石板铺了层红毯。苏晚踩着枫叶往布庄走时,鞋跟踢到块硬硬的东西,弯腰拾起,是片绣着半只枫蝶的布角,布面已经被秋露浸得发潮,针脚却依旧紧实——是去年“针传”时,念念学盘金绣的习作,蝶翅的金线在枫红里泛着暖光,像只停在叶上的活蝶。
“这孩子总说‘蝶要踩着枫叶飞’,”陈砚正往画纸上抹朱砂,笔尖在“秋枫图”的叶脉间游走,忽然指着砚台里的残墨,“你看这墨色,和去年枫树下的冻土一个色,像时光把秋冻成了块墨锭。”他从书架深处抽出本旧画册,册页间夹着片压平的枫叶,是苏晚二十岁那年采的,叶尖的缺口和今年新落的枫叶完全重合,“当年你说‘枫叶的纹路,是老天爷绣的最野的针脚’,现在才算懂了这话的意思。”
苏晚把布角贴在画册的枫叶旁,蝶翅的金线恰好沿着叶脉展开。她取来今年新染的赭红丝线,在蝶翅的空白处绣了串小小的枫果,针脚从翅尖一直排到叶柄,像枫果顺着蝶翅在爬。“野的才生动,”她对着光看针脚的起伏,“就像这枫叶,红得没规矩,才比任何绣品都耐看。”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叠影镜”来了。这镜子由多面镜片组成,正面映着老手艺的物件,反面投射着对应的新创作——修鞋匠的锥子映出3D打印的鞋模,苏晚的绣绷投出电子绘图板的线稿,连念念绣坏的枫蝶,都能在镜中看到补全的翅膀,像新旧时光在镜中相拥。“镜子边缘装了感光条,”年轻人指着条细细的银线,“光线变了,叠影就会换样子,清晨看是老物件的霜,午后是新创作的光,让影子也能跟着日子长。”
苏晚选了母亲的枫纹绣架,架上还留着当年的针孔,她把绣架放在镜前,镜中立刻投出自己现在用的绣架,两架的木纹在镜中交错,她取来金线,在镜边的丝绒布上绣了个小小的“接”字,针脚一半是母亲的盘金绣,一半是自己的乱针绣。“接得住才叫传,”她摸着“接”字的笔画,“不然老的成了古董,新的成了浮萍,两不挨着,多可惜。”
陈砚在镜子的木框上画了串枫果,从框头排到框尾,每个果上都有个针脚印:有的深,是老手艺人的沉;有的浅,是孩子学绣的轻;最末个枫果上,画了只啄果的松鼠,和“槐香信”里那只衔信纸的松鼠是同一只,只是毛色深了些,像换了身秋衣。“枫叶记着秋的红,”他给枫果描边时说,“这些印子记着手艺的重,凑在一起,才是过日子的厚实劲儿。”
立冬那天,“叠影镜”在布庄的枫树下支了起来。补旗袍的老太太把祖母的盘扣放在镜前,镜中立刻映出她新设计的几何扣,新旧盘扣的纹路在镜中缠成串,像条时光的项链;扎风筝的老师傅举着老式竹篾,镜里投出碳纤维的风筝骨,两者的弧度在光里重合,像两代人在同片天空放风筝。
有位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对着镜子拍自己的祖父——祖父年轻时是染坊的伙计,此刻正摸着块靛蓝布,镜中立刻映出年轻人用电脑调的染色参数,布的蓝在镜中晕成片,像把祖孙俩的手都浸在了蓝里。“这是我拍的第一组‘手艺传承’,”年轻人举着相机说,“以前总觉得老的土,现在才知道,这蓝里藏着比任何滤镜都厚的光阴。”
苏晚取来块染坏的枫红布,布上的色斑像片天然的枫叶,她把布铺在镜下,让镜中的叠影落在布上,用银线沿着影子的边缘绣了圈,线迹时断时续,像秋风吹过枫梢的痕。“坏了的地方别遮,”她穿线时说,“让看的人知道,当年的手也慌过,才更敢下手试。”
机器人工程师带着机械臂来了,这次让机器在镜边的布上绣枫纹,机械臂的程序里存着百种枫叶的形状,却特意在某片叶上留了个缺口,和苏晚画册里的老枫叶一样。“学不会的随性,”他在布角贴了张纸条,“但能记住最要紧的缺口,也算懂了点秋的意思。”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阴差阳错……
- 4.8万字6个月前
- 从梦中醒来
- 言情有点偏无限流有点马甲,BG,HE.一切的开始都是因为梦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毕竟只要梦破碎了,人们就完了,所以就要有人去付出,把破碎的梦......
- 3.8万字5个月前
- 沈总你老婆跑了
- [虐恋+非女强+替嫁]【乖巧冷清性格直白替嫁千金】X【卑鄙无耻口是心非不着家的大少爷】“晚晚,你喜欢我?”祁晟看着面前只穿着睡衣的女人,看似......
- 2.1万字4个月前
- 一念终不归
- 以姜苒和为主角,讲述着关于她的一生
- 1.0万字4个月前
- 秋光藏在他的眼膜里
- 那个秋天,风温柔得不像话,带着熟透的桂子香气,轻轻抚过街道的每一处角落。我像往常一样走过那条铺满金黄银杏叶的小路,不经意间抬眼,就撞进了他的......
- 0.4万字4个月前
- 代价(裴闵x裴芙续写)
- 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Choyoo77老师对不起!!!)衍生|伪骨科|改编
- 0.5万字2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