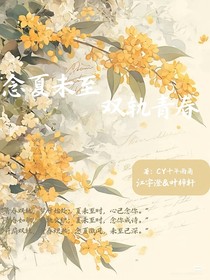新绿与旧痕 (2-1)
雨水的清晨,回春巷的泥土里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苏晚蹲在梅树下翻土,指尖触到块硬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是个小小的磁贴,吸着半根绣线——是去年埋的“手艺盲盒”底掉出来的,线的颜色是念念最喜欢的鹅黄,针脚还缠着点冻土,像裹着冬天的尾巴。
“这是念念埋的‘约定盒’里的,”陈砚正往画纸上抹淡墨,笔尖在“春醒图”的梅枝旁顿了顿,纸上的新绿忽然让他想起什么,转身从书架上取下本泛黄的绣谱,谱子的最后一页贴着片干枯的柳叶,是苏晚十岁那年夹的,“你看这叶脉,”他指着柳叶的纹路,“和今年刚冒的芽一模一样,像时光打了个结。”
苏晚把磁贴凑到阳光下,鹅黄的绣线在晨光里泛着暖,线尾的冻土慢慢化成水,在谱子上洇出个小小的圈。她取来新抽的蚕丝,把断了的线接起来,接痕处故意留了截松散的线头,像柳芽刚抽的绒毛。“旧线不能全接死,”她对着光看线头飘动,“得让风带着走,才知道新绿长在哪。”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时光绣布”来了。他们用特殊的布料做了块巨大的画布,布料遇光会显旧痕,遇热会现新纹——把老照片投影在布上,布面就会浮现对应的针脚;用手捂住旧痕,新的纹样就会从指缝里冒出来,像新绿顶开冻土。“我们在布边缝了圈传感器,”年轻人指着布沿的银丝,“谁路过时说句话,声音就会变成对应的色线,织进布尾的空白,让路过的风都带着故事。”
苏晚选了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正坐在梅树下绣柳叶,苏晚把照片投影在布上,布面立刻浮现出盘金绣的针脚,她取来嫩绿色的丝线,在针脚的间隙绣了串小小的芽,针脚从梅枝一直排到布边,像新绿顺着旧痕在爬。“老故事得有新邻居,”她擦去布上的水痕,“就像这梅树,守了多少年,也得等柳叶来作伴,才够春天的意思。”
陈砚在“时光绣布”的角落画了串符号:有的像墨滴,有的像线轴,最末个是只衔着柳叶的蝉,和去年“蝉夏织梦”时的荧光纹样重合。“符号记着旧日子,”他给符号描边时说,“新纹长着新日子,凑在一起,才是光阴的全乎劲儿。”
惊蛰那天,布庄的院子里挤满了人。白发老先生把年轻时的修鞋工具放在布前,布面立刻显出土黄色的针脚,像锥子扎过的痕迹;扎风筝的老师傅用手捂住布上的旧风筝,指缝里立刻冒出只新风筝,翅膀上的纹路是念念去年画的;连刚会走路的小孩都被抱过来,小手按在布上,竟印出串小小的脚印,和长卷上念念绣的那串一模一样。
有位推着轮椅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让护工把布推到“盘金绣”的旧痕旁。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只绣了半只的蝴蝶,翅膀的针脚和苏晚母亲的手法如出一辙。“这是当年和你娘一起绣的,”她对苏晚说,“她说‘等绣完这只就一起去看柳’,结果我病了,没等她下针。”
苏晚蹲下身,让老太太握着她的手,一起把蝴蝶补完。老太太的手已经没了力气,针几乎握不住,苏晚就把着她的手腕慢慢走,新针脚和旧针脚缠在一起,像两只蝴蝶在新绿里并排飞。
“这下能一起看柳了,”老太太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泪,“比当年想的还热闹。”
机器人工程师带着机械臂来了,这次让机器学“时光绣布”的脾气——对着旧痕喷冷水,旧针脚就更清晰;吹热气,新纹样就长得更快,机械臂绣出的柳叶带着规律的顿挫,却在叶尖添了个小小的弯,是机器算出来的“跟风走的弧度”。“学不会的随性,”他在布边贴了张纸条,“但能学会等风,也算懂了点春天的意思。”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莹火森森
- 男主晚年知悟女主两世只知心灰意冷只爱一人无依无靠社会上只与男主一人牵扯但女主仍坚守本心重生文不是大女主文,人生在世只靠自己外来因素互帮互持。
- 0.2万字7个月前
- 念夏未至,双轨青春
- 在那个被阳光温柔拥抱的小镇上,夏天似乎总是带着一丝未完的遗憾,缓缓铺展在青春的画卷上。故事的两位主角,林念辰与苏夏辰,名字中各自蕴含着对季节......
- 3.2万字6个月前
- 风吹南阳
- 少年不知爱何起,风吹南阳留住你
- 0.3万字5个月前
- 拾伍年
- 从2008年校园初遇到2023年婚姻破碎,十五年感情在生日当天迎来终章
- 0.7万字4个月前
- 京城团宠
- 洛小熠和百诺有了三胞胎儿子后,又有了一个小女儿,这是六大家族中唯一的女孩,所有人都争着宠,本文以安安为主,安安的身份又会是什么呢?……后期会......
- 4.6万字2周前
- 我在榕树下等你
- [双男主+白切黑+甜宠+马甲]
- 0.5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