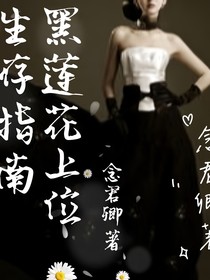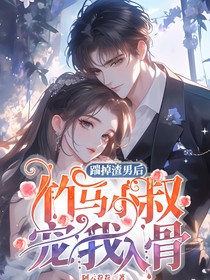梅香与新约 (2-1)
冬至的雪落得绵密,回春巷的老梅树裹了层白。苏晚推开窗时,正看见枝桠上的梅花被雪压得低低的,花瓣的弧度竟和传针盒里那半朵盘金绣的梅瓣重合。她取来竹篮,踩着薄雪去摘初开的梅,指尖触到冰凉的花瓣,忽然想起母亲说过:“冬酿的酒里得落两朵梅,才够劲儿,就像针脚里得藏点硬气,才立得住。”
陈砚正给“针脚图谱”补注,笔尖在“盘金绣”三个字旁顿了顿,转身从柜顶取下个陶坛,坛口的布巾上绣着朵小小的梅,是苏晚刚学绣时的手笔,针脚歪歪扭扭的,却把梅蕊绣得格外鼓。“这是你十八岁那年酿的青梅酒,”他揭开布巾,酒香混着梅香漫出来,“当年你说‘等我绣会了坛上的梅,就让这酒开封’,结果绣了改,改了绣,酒倒存成了老酿。”
苏晚把新摘的梅放进坛沿,花瓣上的雪融成水珠,滴进酒里,泛起细碎的涟漪。她取来去年续的新针,在布巾的空白处绣了串小小的酒滴,针脚从坛口一直排到梅瓣,像酒顺着针脚在流。“老手艺得有新滋味,”她对着光看针脚,“就像这酒,存得再久,也得添朵新梅,才够鲜活。”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手艺盲盒”来了。他们把传针盒里的旧针、老绣线、甚至梅树下的冻土都装成了盲盒,每个盒子里附张“寻踪卡”,卡上画着线索:断针旁标着“盘金绣的转弯处”,冻土上印着“梅树根下的针脚香”,让拆盒的人跟着线索找对应的老物件,听它的故事。
“我们在盲盒底留了块磁贴,”年轻人指着盒底的小铁片,“找到故事后,就能把自己的小物件吸在上面,比如根新针、片绣坏的布,让盲盒变成会长大的故事书。”
苏晚选了片母亲绣坏的梅瓣,用红绸布包起来,放进最老的盲盒里。布包上绣了个迷你的“苏”字,针脚和母亲当年的盘金绣如出一辙。“坏了的也值钱,”她说着把盒盖扣紧,“就像摔碎的瓷,粘起来的缝里,藏着比原来更密的心思。”
陈砚在“寻踪卡”的背面画了串脚印,从盲盒一直延伸到梅树下。有的脚印深,是捧着故事的沉;有的浅,像孩子追着梅香跑的轻;最末个脚印旁,画了只衔着绣线的鸟,翅膀的纹路和念念去年画在针谱里的那只一模一样。“盲盒会跑,”他给脚印描边时说,“但脚印能把故事拽回来,就像回春巷的雪,再厚也盖不住石板路上的辙。”
小寒那天,盲盒在梅树下开盒。修鞋匠拆开冻土盲盒,从梅树根下挖出块磨秃的锥子头,说:“这锥子扎过的鞋,比这树的年轮还多;”扎风筝的老师傅拆到断针盲盒,对着“盘金绣的转弯处”找了半天,最后在母亲的绣架木棱上找到了对应的针脚,忽然红了眼眶:“这转弯的劲儿,和当年教我的时候分毫不差。”
有个穿校服的姑娘,拆到了苏晚放的梅瓣盲盒。她从书包里掏出个绣绷,绷上的梅只绣了半朵,针脚歪歪扭扭,却和母亲绣坏的那片格外像。“这是我太奶奶留下的,”她指着绣绷说,“她说‘等我绣完这朵,就带你去回春巷学绣’,结果没等绣完就走了。”
苏晚握着姑娘的手,一起把那半朵梅补完。姑娘的手抖得厉害,针脚里总带着急,苏晚就教她“像喝这坛老酿,得慢慢品”,补到最后,新针脚和旧针脚缠在一起,像两棵梅树在雪地里并立。
“这下她能看见了,”姑娘放下针时,睫毛上沾着雪,“比她想的还好看。”
机器人工程师带着机械臂来了,这次让机器拆了个盲盒,里面是片绣坏的兔子耳朵。机械臂跟着针脚的轨迹学绣,绣出的兔子歪得更厉害,却在耳朵尖添了个小小的梅花结,是机器自己算出来的“温柔补偿”。“学不会的急,”他在卡上补了行字,“但能学会等,也算种进步。”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隐藏在时光的爱
- 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在时光的长河中缓缓流淌。他们在生活的波折中相互扶持,最终在岁月的沉淀中找到了属于彼此的幸福。
- 1.5万字6个月前
- 黑莲花上位生存指南
- 花瓶疯美人?我有的只有你们永远都到达不了的高度
- 5.8万字6个月前
- 我们生生不息
- 桑野×沈词序再婚的妈,去世的爸,虚伪的家人,厌世的她。自杀的妈,酗酒的爸,烦人的亲戚,乖戾的他。沈词序第一次遇见桑野是在怀城,少女身穿一件淡......
- 3.5万字6个月前
- 我的社畜日常与奇妙桃花劫
- 林晓悠,一个在广告界摸爬滚打、怀揣创意梦想的小透明,乐观开朗,却被“外星人广告”这一离谱需求折磨得焦头烂额。一次行业交流派对上,她冒失撞翻顾......
- 7.9万字5个月前
- 踹掉渣男后,竹马小叔宠我入骨
- 黎语枫把全部青春都给了谢倦铭,可一场车祸让他看清了这个男人。被出轨后,她当机立断决心离开。没想到上一秒分手,下一秒就遭遇到竹马小叔的恋爱邀请......
- 28.8万字5个月前
- 尹妹:朋友还是恋人
- 〈禁止上升〉你与我朋友还是恋人
- 0.1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