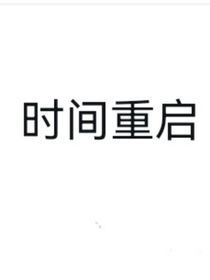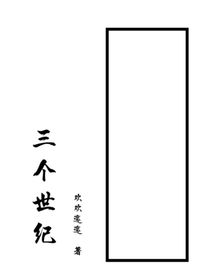第一章初嗅肉味 (4-1)
冰河两岸,云杉树森然林立,宛如蹙眉。树上挂着的白霜刚被一阵寒风吹落,树枝斜坠,相互依偎,在渐暗的天光中,黑魆魆的,似有不祥之气。
无边的沉寂笼罩着大地。大地更是一片凄凉--死气沉沉, 不见动静,寂寥冷清--就连大地的神情也愁苦惨。
这片妻凉的大地仿佛暗藏一丝笑意,但这笑意却比悲伤更可怕--就像斯芬克斯的微笑那样忧伤,又如寒霜一样冰凉,带着几分不可一世的霸气。它是高高在上、不可言喻的不朽智慧, 似在嘲笑生命的徒劳和求生的无望。它是荒野,是野蛮,是天寒地冻的北国荒原。
然而在这荒原之上,到处是不屈的生命。冰河上,一群狼狗正在费力前行。它们的气息刚一呼出就立刻凝聚,化作气沫四散飞溅,落在粗硬的毛上,结成晶莹的冰霜。狼狗身上套着皮轭,轭上连着皮绳,头系着雪橋,狼狗拉着雪橇在雪地上费力前行。雪橇是用坚硬的桦木做的,没装滑板。它的前端上翘,形如纸卷,为了能从前方波浪般涌起的柔雪上压过。雪橋上牢牢捆着一只狭长的木箱,还放着别的东西:几条毛毯、一把斧头、一只咖啡壶和一口平底锅。但最显眼的,是那只狭长的木箱,占去大半个雪。
狗队前,一个穿着宽大雪地靴的男人在艰难前行。雪后, 另一个男人在费力跟进。雪橇上的木箱里,还躺着一个男人,他的劳役已经结束--他已被荒野打垮,再也无力挣扎,不能行动。荒野从不喜欢有人行动,但生命总是冒犯荒野,因为生命在于运动,而荒野的目的就是摧毁运动。它冻结江河,不让流水归入大海;它逼出树木的汁液,直至坚硬的树心也被冻结。而它最残暴恐怖的一面,则是欺压人类使之屈服--而人类,又是最不安分的生灵,总是忤逆自己的格言:一切运动终将停止。
可是,两个男人的生命并没停止。他们无所畏惧,不可战胜,一前一后,正在雪地里艰难前行。他们身上裹着鞣制的皮袄,嘴里呼出的气息已凝聚成霜,睫毛、脸颊和嘴上已结成晶莹的冰凌,面孔无法认清,俨然戴着鬼面具,仿佛幽冥地府为鬼魂举办葬礼的差役。但在面具之下,又的确是两个活人,穿行在荒凉沉寂又仿佛在嘲笑他们的雪地上。而这两个渺小的冒险家,却执意要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冒险,以其微弱的身躯对抗威力无比的冰天雪地;但冰天雪地却像太空深渊,遥不可逾,陌生诡异, 了无生气。
他们一路走来,默默无语,为了节省力气。四周一片沉寂, 仿佛触手可及,压在他们心头。这股压力之于他们的心灵,犹如深水的压力之于潜水员的身体。他们承受着漫无边际的压力,无法抗争,心灵被压入灵魂深处最幽僻的一隅复又压出。犹如葡萄榨汁,将人类灵魂中一切虚假的热情、得意和自负,统统挤压出去,直到他们发现,原来自己竟是如此渺小卑微,如同尘埃微粒,在许多大而无形的元素和各种自然力的交互影响下,仅凭一点小把戏和小聪明苟且前行。
一小时过去,又一小时过去。短暂无日的灰暗天光开始消退。一声微弱的嗥叫从远方响起,回荡在宁静的夜空。骤然升高,达到极限,悸动慌张,延续片刻,又逐渐消失。叫声带有俄狼似的凄厉凶猛,不然人会以为是亡灵的哀号。前面的男人转过身来,与后面的男人遥相对望,两人隔着狭长的木箱,彼此点头示意。
叫声再次响起,如针一般尖利,刺破宁静的夜空。两人都已听出叫声在哪里,就在身后他们刚刚走过的那片雪域。叫声复又响起,是应和的叫声,同样是在身后,却在刚才那个叫声的左侧。
“比尔,它们追上来了!”前面的男人说。 声音听来嘶哑失真,分明已用尽气力。
“肉不多了,”后面的男人说,“几天来,连只兔子的影子都
没看见。”
两人不再言语,侧耳倾听身后接连传来的嗷嗷捕猎声。
白牙(WHITEFANG)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