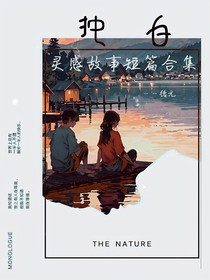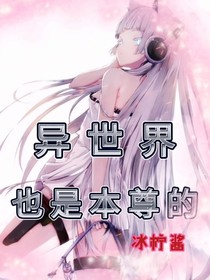哲学(三)
第二种可能的回应是主张,基于“后果主义要求过高”这点而反对后果主义的那些人,他们在实践推理中给予道德的重要性过大。(Brink 1989; Wolf 1982, 1992)。如果道德的考虑主导了实践推理,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在决定我们的行为时是唯一的,或者至少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考虑,那么后果主义会由于要求太高而站不住脚。但如果我们把后果主义道德的极端要求放在实践理由和要求框架中的恰当位置,那么它就不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借大卫·布林克之言,有关 “后果主义倾向要求过高”的“道德担忧”(moral worries),可能实际上是“对道德的担忧(worries of morality)”,即“我们是否有理由按道德要求来行事”的担忧。然而,这一策略所预设的那种道德的看法是否为真,这一点是存疑的。至少,大部分把后果主义当作一个道德规范理论并为之辩护的人,应该都不希望后果主义被视为一个经常或容易被压倒或者忽视的理论(参见 Railton 1984, Miller 1992 第10章, Jollimore, 2001 第3章)。一个可能的例外是诺克罗斯(Alastair Norcross,2006a, 2006b),他提出了一种修正的后果主义,他称之为“标度(salar)效用主义”。这一修正理论根据道德正当性对行为进行排序,但并不声称哪个行为是被要求的。他宣称,因为标度效用主义把正当性看成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一个二元属性的问题,并且拒绝确定某个行为是被要求的,因此它避免了要求过高和一些相关反驳。
第三种策略应该是最有名且最经常被应用的。这一策略主张,基于有关人类本质和行为者能力的那些合理且准确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后果主义所要求的生活并不是完全不同于我们当下所过的那种生活。相反,后果主义(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要求对我们当前生活进行合理而且微小的调整。尤其是有人主张,后果主义允许行为者偏向自己的规划与关切以及一些其他个体(朋友、家庭成员等等),并且这一切都与行为者把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压倒性计划是一致的。这一论说的经典章节在密尔的《效用主义》中:
我们不能总是指控说,效用主义的反对者从一个可耻的角度展示效用主义。相反,那些对其无偏向(disinterested)的特征持有正义看法的人,他们有时也会指责说,其标准对于人类来说过高。他们说,要求人们总是按照公益最大化的诱因来行事,这要求太高了。但这误解了道德标准的意义,并且混淆了行为的规则与其动机……相当大一部分行为的意图,它们并不是为了世界总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而世界总的利益由个体的利益组成。在这些情况下,最为道德的人在这些场合下的考虑并不需要超越具体的相关人,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但也要确保自己在有益于他们时,不要侵犯任何其他人的权利——即他们合法且有权得到的期待。根据效用主义道德,幸福的增值就是道德的目的:个人能在更大范围内使幸福增值的情况,即成为一个公共施惠者的情况,都只是例外(千里挑一);并且在只有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行为者才被要求考虑公共效用;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私人效用,即小部分人的利益或幸福,就是他要考虑的全部。(Mill 1992 [1861], pp. 64–66.)
甚至葛德文(1801 [1968])也认同了这样的论证版本,他写道:
真正的智慧也给我们推荐个人性情感……因为创造幸福就是道德的目的,还因为那些生活在家庭关系中的人,他们有很多创造幸福的机会,虽然繁琐利小,但总量并不少。(引自 Cannold, et al., 1995)
(后文将会提到,这一立场与2.3中葛德文的极端得多的后果主义立场存在一些冲突)。
这一论说的更新版本遵循密尔的基本策略。雷尔顿(Railton, 1984)主张,一个“精致”后果主义者会发展出一套决策模式,按照这一模式,除非少数特殊情况,他一般不会提及后果主义目标,这样的个体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外显的行为上,与非后果主义者都会十分相似。杰克逊(Frank Jackson,1991)也同样主张,对全心全意的后果主义者而言,其最有效的策略是聚焦于由具体个人组成的小群体,包括与其他个体形成亲密关系,而不是去努力增进全人类的福利。贝尔斯(Bales,1971)、布林克(Brink 1989)、佩蒂特和布伦南(Pettit & Brennan,1986)等人,也采用这一论证的各种版本。
我们很难评价这种后果主义策略。后果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过度沉迷于后果主义策略很可能从某个点就变得适得其反,因此,稳妥的建议就是后果主义行为者要去发展更为温和的进路。另一方面,密尔与很多其他后果主义者,似乎都低估了一个全心全意的后果主义能够做出的贡献,因此低估了该行为者可以被要求做出的贡献。不仅如此,自密尔以来,我们影响陌生人生活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加了。正如苏珊·沃尔芙(Susan Wolff)所写,“根据我们所处世界的经验性环境,这一论证就是不令人信服的。拥有全面且丰富的生活,这对个人和其邻居带来的幸福,相对于做一个道德圣人,全身心奉献于救助病人、被欺压者、饥民和无家可归者,由此带来的普遍幸福,两相比较,前者的数量小得可怜。 (Wolf 1982, p. 428; see also Singer 1972)。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经验事实的证实。如果我们考察真正的“有效利他主义者”,他们全身心地献身于产生尽可能多的福利,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类人感到确实有必要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在时间、金钱、舒适度、私人关系和个人幸福等方面做出巨大牺牲(例子见 MacFarquhar 2015)。
不仅如此,即使如雷尔顿的精致后果主义这样的理论,它允许精致后果主义行为者有意不去最大化利益,该理论还是必须坚持认为,这样的具体行为在道德上确实是错误的,而这种坚持与我们的道德直觉也是冲突的(Jollimore 2001)。进而,并不清楚的是,诉诸人类能力的各种限制,就真能成功地将一个根本上激进的理论转变为一个适当保守的理论。
3.3后果主义不偏不倚性与正义
除了声称后果主义不偏不倚性要求过高外,很多批评者还认为,它允许的也过多。后果主义使得行为是否可允许的依据,完全在于行为后果的价值,这就意味着,基于后果主义,没有任何类型的行为会被彻底禁止。(当然,除了根据次佳后果而定义的那类行为。)因此,基于后果主义,折磨、蓄意谋杀、强奸和其他侵害基本人权的情形都至少是潜在地可辩护的;从道德上讲,没有任何这样的行为是会被排除的,除非它造成事态的相对价值如此决定。
正如之前的那种反对意见一样,这一反驳的效果并不在于否定后果主义是不偏不倚的,而在于认为它包含错误类型的不偏不倚性。举个文献中常见的例子:为了阻止公众骚乱,后果主义会推荐去定罪并且惩罚无辜者。按照日常直觉,这样的行为就是公然违背正义,而且,“这种建议源于不偏不倚的计算,而且这种计算平等地考虑了每个人(包括那个被陷害的人)的利益”,这种回应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尽管严格地说,这种主张是属实的,但是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仍存在清楚且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我们得出这一结论:那个被陷害的人并没有得到不偏不倚的对待。我们希望司法(正义)体系实施惩罚的根据是罪行的程度,而不是每个案例中后果为社会带来的预期利益。而且,两种方式都构成了不同形式上不偏不倚的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方式在道德上是同等可接受的。
后果主义者对此有很多种的回应方式。最常见的回应与要求过高反驳的回应一样,主张对于类似规则和实践的东西,它们可以在后果主义基础上得到辩护。这一回应的经典版本可追溯到密尔的《效用主义》(1992 [1861])。密尔主张,如果要给予司法(正义)机构以一个总的辩护,那么辩护基础一定在于其对社会的效用。因为,正义除了服务和保护我们的利益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它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呢?但是既然正义体系要想成功地履行这种角色,就要受辖于这样的常识原则,比如,只有有罪的人应该被惩罚,罪罚相配等,这就意味着这种原则根本不反对后果主义。相反,在最深的辩护层次中,后果主义与正义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也可见 Neilsen 1972)
“这种耦合是普遍存在的”这种主张很可能是容易确立的。对密尔以及其他后果主义者而言,挑战出现在那些没有这种耦合性的特定情形。假设即便这种情形有可能存在,一个人也不会简单地放弃后果主义,转而支持一些对正义更加亲和的观念(比如密尔本人有时会支持的规则后果主义)。在这一假设之下,仍存在两种供后果主义者使用的一般性辩护策略。第一种策略辩称,即便正义要求和后果主义要求之间的耦合失败,仍有好的后果主义理由成为一个尊重正义命令的后果主义行为者(Pettit 1997; cf. Railton 1986)。第二个策略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不正义的事情可以得到后果主义的辩护,但是认为,只要情况是如此,那么正义必须为后果主义要求让步(Smart 1973; Kagan 1989; Pettit 1997)。由于日常的正义直觉有着如此明显的深度和力度,这两种进路是否充分的争论仍然是持续不断的。
4 道德不偏不倚性II:义务论道德理论
4.1 义务论不偏不倚性和个人视角
3.2节表明,虽然“道德应该是不偏不倚的”这一要求可以做出后果主义的诠释,但这绝不是我们可以做出的唯一诠释,也不显然是最可行的诠释。3.3节中关于正义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回想那个受诬的无辜者,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他的根本利益被牺牲了。他很可能会控诉说:他没有得到恰当的不偏不倚对待。尽管在计算整体利益时,他的利益的确得到了考虑,但最终他也的确受到了粗暴且冤枉的虐待。他的控诉还可以有如下的理由:如果他有选择的机会,他绝不会赞成一个允许任何人被如此对待的道德体系。因此,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利益得到了平等对待,但在另一种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他的利益——以及或许更重要的他的权利——似乎根本没有得到充分或恰当的考虑。
许多义务论者坚持认为,后果主义错在没有把道德行为者作为个体来重视。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后果主义“并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分别”(Rawls 1971,第 5 节)。(罗尔斯主要针对的是效用主义,但这一点可以运用得更广。)赫雷(Paul Hurley)写道:“除非我们认识到人是有独立的道德意义的,否则道德就会以非个人化观点奴役我们。承认个人具有独立于非个人化道德意义之外的道德意义,这对于保证道德要求具有理性权威,并防止道德以非个人化立场奴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Hurley 2009, 178)。谢弗勒表示:“对于人类这一拥有价值观的生灵而言,某种偏倚性拥有规范性力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道德要普遍或系统地拒斥偏倚性,这就和我们作为评价性生物这一本性相悖逆。在我看来,这会让道德变成一种不融贯的事业。”(Scheffler 2010)
因此,后果主义不偏不倚性会对个人提出超常且在许多人看来不合情理的要求(3.2节),这一事实可能表明后果主义没有认真地把个体看作行为者。同时,后果主义不偏不倚性允许将个人用作促进更大利益的纯粹手段(3.3节),这一事实可能表明后果主义没有认真地把个体看作受动者(patient)。义务论者偏好的那种不偏不倚性观念,拒绝把不偏不倚的行为看作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或其他种类的非个人化的善),从而避免有这样的蕴含。义务论者将正当而非善作为道德的根基,并倾向于认为,道德行为就是符合那些能为所有人合情理地接受的原则的行为。
这些原则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要如何确定它们,义务论者对此有分歧。但是,义务论者似乎有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共识:道德不偏不倚性并不要求行为者做常规决策时,在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之间保持严格中立。相反,根据义务论的观点,行为者可以更为关心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某些特殊情况才可能要求不偏不倚——例如负责招聘,参加陪审团,给学生的论文打分,或设计法案——但在日常决策和行为中,不偏不倚性并不是一般性的广泛要求。这在某种意义上会限制不偏不倚性的范围和要求;但这并不妨碍义务论者将不偏不倚性视为道德不可还原的核心。毕竟在许多义务论观点中,允许行为者在日常层面(对自己和亲友,对自己的目标等)有所偏倚的那些规则,是通过直接诉诸不偏不倚的考虑而得到辩护的。例如,义务论者可以认为,尊重每个人的自主和尊严的最好办法——自主和尊严被认为是所有人平等拥有的道德特征——是在我们的道德规则中允许每个人都有空间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并照顾自己的私人关系。在这些目标和关系中,不偏不倚的要求一般是不适用的。这就是说,一阶偏倚性与二阶不偏不倚性是相容的(Barry 1995;另见 Hooker 2010)。
义务论通常允许(某种程度的)一阶偏倚性,即允许行为者更为关心自己的利益、计划和亲人。这点并不能被看作蕴含着,行为者本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利益在客观上更有价值,或者行为者这么看是有道理的。相反义务论者会说这反映了这个事实:行为者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视为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这是合乎道德的(或许,再次,这是因为它能得到二阶不偏不倚性的辩护)。因此,义务论的道德体系往往包含一种不可还原的行为者相对性,而这是后果主义理论所拒斥的(Nagel 1986; McNaughton & Rawling 1992, 1993, 1998; Jollimore 2001; Kamm 2007 )。
义务论理论纳入这种行为者相对性,从而可以避免一种直截了当的“对道德行为者要求过高”的反驳。尽管如此,义务论理论还是会受到其他版本的“要求过高”反驳。例如,有人认为,康德主义坚持认为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从而使得在私人亲密关系中通常(或许是必然)起作用的那些动机变得不合道德,甚至被禁止。(Stocker 1976;Williams 1981)。康德主义者的回应通常是使自己远离“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这一主张,反而承认“出于义务的要求”只是一个限制条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应作为动机的主要来源(Baron 1995)。当然,道德价值的康德式论说对义务论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些不采取康德式道德价值观的理论,很可能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个“要求过高”反驳。
4.2 不偏不倚性和可普遍化
许多义务论观点,尤其是康德主义的观点,非常看重道德不偏不倚性,原因在于可普遍化这一概念在这些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Gert 1998; Hare 1981; Kant 1964 [1785]; Kohlberg 1979)。粗略地说,要求道德判断是可普遍化的,就是要求道德判断独立于任何特定视角。如果一个行为者判断 A应当在S情况下做X事,那么不管她是否碰巧就是A,或者是这个情况(或许会受A的行为的直接影响)涉及的其他人,或者是完全中立的旁观者,都应当愿意做出同样的判断。这个行为者的具体身份与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或适当是完全无关的。
如此表述的可普遍化确实至少蕴含一种不偏不倚性:如果一个行为者的判断是可普遍化的,那么他就是道德上一致的;这就是说,他会用同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与他人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者不会为自己破例,不会允许自己违反自己认为要约束他人的规则,不会去做那些自己不会接受他人去做的行为。然而,这种不偏不倚性并不必然是针对其他人的利益、权利或要求权而言的。如果对可普遍化作最低要求的诠释,那么一个拥有种族主义价值观念——某些种族的福利客观地比其他种族的更(或者更不)重要——的人,他的判断很可能也是可普遍化的,只要他确信自己的判断是客观地正确的,从而所有人,包括那些因这些观点被普遍采纳而受损的人,都应该同意这个判断。(参见 Gewirth 1978, 164; Gert 1998, Chapter 6; Wiggins 1978; Williams 1985, 115)。
然而,种族主义者的判断是可普遍化的,这一结论预设了一种要求极低的可普遍化论说。基于这种论说,可普遍化只要求行为者(从自己现在的视角出发)真诚地承诺自己的判断具备客观性,意思是从所有视角看这个判断都是正确的,由此可以要求所有人赞成它(无论他们实际上是否赞成)(Cf. Parfit 2011, I, 323–24) 。有两种方法可以提高可普遍化要求。第一种是诉诸反事实性主张:如果A确实身处各个视角,那么A会做什么的判断。A的某个判断是可普遍化的,当且仅当A不仅在当前视角下认可如此判断,而且在其他任何视角下都会认可。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可普遍化,那么种族主义者的判断是可普遍化的概率就会小得多,实际上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当人们自己就是种族R的成员时,他们一般并不会采纳这样的一种观点:种族R成员的福利没有其他种族成员的福利那么重要。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很可能要求太高,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道德判断或原则,会得到任何既定行为者在每一个视角上的赞成。
另一种可普遍化的进路完全避免诉诸心理事实,认为某一具体判断是否可普遍化是一个逻辑事实,而非心理事实。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检验认为,可普遍化是正确道德判断的独特特征;一个道德判断是可普遍化的,当且仅当它可以毫无矛盾地被意愿成为普遍的实践法则(Kant 1964 [1785])。这个检验的关键在于意愿某个道德判断成为普遍法则是否会导致矛盾,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某个判断是否是可普遍化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而不取决于这个判断恰巧涉及到哪些具体的人。
相对于可普遍化只要求形式一致的最低要求论说来说,这两种要求更高的论说所蕴涵的那种不偏不倚性,其要求更有实质内容。例如,康德似乎认为,可普遍化蕴涵了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或仁爱心,这表现为我们对他人负有不完全责任。然而,康德对这一点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具体来说,目前尚不清楚,当我们意愿“当别人有困难时,我总是不理会他们”这样一条法则时,这如何能导致任何矛盾。诚然,假如由我们来选择所有理性者都应遵守的普遍法则,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我们自己也可能需要他人的援助。但是,说意愿它成为普遍法则是不明智的,并不等于说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此外,正如威金斯(David Wiggins,1978)指出的,某些看起来应在道德上被允许的行为,比如出于慷慨而免除债务的行为,其准则似乎不能通过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这些例子表明,这些从可普遍化推出不偏不倚性的方法有一个通病:至少基于康德主义诠释,可普遍化是道德判断的一个形式属性;然而如我们所见,道德不偏不倚性是一个实质的而非形式的概念。(参见 Herman 1993 和 Korsgaard 1996 回应这些问题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