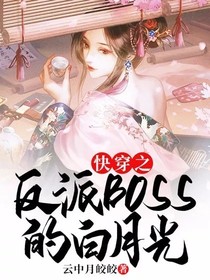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二) (5-2)
当然,不管是正常主体还是反常主体,其实都是知识主体,也都是权力主体,因为经验、知识和权力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结构在任何地方都是大体一致的。《性欲史》第2卷和第3卷关注快感体验,它导致的是自身技术意义上的审美主体的诞生。尽管如此,“性欲”还是与其他任何体验一样进入了“词”与“物”的复杂游戏之中:知识(真理)的形成、权力的实施和主体的诞生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关于性欲经验的描述和解释表明:“个体不得不把自己作为一种‘性欲’主体来认识,这一主体向非常多样的认识领域开放,并且与一个准则和约束的系统连接起来”[20]。当然,这里的权力是由自己而非别人施加的,针对的也是自己而非别人。
后期现代性或者说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使我们陷入了“人类学迷梦”。从福柯对萨特的批判可以看出,他期待这种现代性退出历史舞台,而20世纪60年代是新断裂的开始。“萨特倾其全力把当代文化,即心理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的各种既有收获整合到辩证法中。但特定的情况是,他不可能不把分析理性所揭示的、从深层次上构成为当代文化一部分的一切东西:逻辑、信息理论、语言学、形式主义弃置一边。《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19世纪的人为思考20世纪而作出的充满魅力的、哀婉动人的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萨特是最后的黑格尔主义者,我甚至要说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21]
这无疑是把萨特看作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是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最后的守护者。福柯认为自己以及同时代的人仍然处在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中,尽管现代性已经接近其尾声。那么如何定位福柯本人的姿态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现代性的反思者。但说他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则似乎过于突出了其批判的锋芒,而削弱了其建设性的努力。“建设”并不意味着系统性的建构,他有关“反现代性”的描述往往是片断化的、琐细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要问:如果说现代性之前是古代性,那么现代性之后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是反现代性呢?
三 当代性的可能维度
福柯不是“用现在的术语写过去的历史”,而是“写现在的历史”。[22]这就引出了他在两个《何谓启蒙?》文本中所说的关于“现在”的提问法。在第一个文本一开始,福柯这样表示:“在我们的时代,当一家杂志向其读者们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它是针对每个人都已经有其看法的某个主题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它不会冒险去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在18世纪,它会愿意向公众提出一些人们正好还没有答案的问题。”[23]福柯显然就“当代人”与“现代人”的姿态进行了一种区分:当代人始终不会偏离现在,而现代人则愿意面对未来。真正说来,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梅洛-庞蒂,现代思想家都关心未来,他们往往为了“未来”而反思“现在”;这似乎与古代思想家的旨趣大不相同,后者并不关心“现在”,他们关心的是“过去”,或者说“现在”只不过是过去的“延续”。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快穿之反派boss的白月光
- 第一个世界(完):把温柔哥哥撩到手了第二个世界(完):那个将军在替我守墓第三个世界(完):在末世我抱紧了大腿第四个世界(完):我是被偷换的真......
- 28.9万字1个月前
- 喜羊羊之杀手回来
- 0.4万字1个月前
- 83号疯人院
- 湫白在经历一场车祸后,睁眼到了83号疯人院,遇到了各色院友,昱宁说院里每个人都有点小癖好,然后,湫白看到:牧昭在厨房里徒手熔金;屿白的腿变成......
- 6.6万字1个月前
- 江澄变小了
- 0.1万字1个月前
- 小花仙冬季篇(自创)
- 初代和二代花仙魔法使者一起收服冬季节气花信
- 0.6万字1个月前
- 穿越之妖怪的救赎
- 江夏蝉:“我是金蝉子转世?还是天女?!怎么可能?!”观音:“可是这就是事实”,江夏蝉:“我什么我要和我的前世抢男人?”,齐天:“无论你是谁,......
- 14.5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