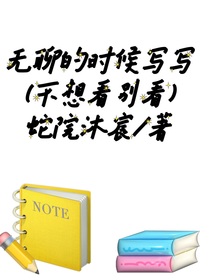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一) (6-2)
我们不妨大体勾勒一下福柯关于时代的基本划分。他在《疯癫史》正文一开始就断言,在中世纪末期,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他进而表示,从14至17世纪,也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麻风病留下的意味着“净化”和“排斥”的空间等候并召唤罪恶的一种“新化身”:虽然“麻风病消失了,麻风病人差不多从记忆中被抹掉了”,但其排斥和净化的“结构仍然保持着”,“穷人、流浪汉、轻罪犯者、‘精神错乱者’”很快就会恢复“麻风病患者抛弃了的角色”;麻风病的接力棒最初其实是由性病接手的,但“在古典世界里承担麻风病在中世纪文化里面之角色的”不是“性病”而是“疯癫”,即在麻风病消失两个世纪之后,疯癫和它一样引起了“区分、排斥和净化的反映”;当然,疯癫并非一开始就受到排斥,“在疯癫于17世纪中叶没有被主宰之前,在人们为了它再度复活各种古老的仪式之前,它曾经顽固地与文艺复兴的全部重大体验联系在一起”[1]。
至少按照《疯人船》对其最单纯、最具象征性的形象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文艺复兴世界的想象空间中,飘泊不定的疯子还有某种边缘性地位,在疯癫与理性之间可能的对话渠道还没有被斩断。然而在17世纪以来的古典世界中,它已经受到了完全的排斥,变成了绝对沉默的他者——“古典时代将以一种奇异的猛烈打击,让文艺复兴时代刚刚解放了其声音但控制了其暴烈的疯癫归于沉默”[2]。
笛卡尔哲学无疑最典型地代表了古典哲学,它试图通过普遍怀疑来确立全新的起点。这种回到内在理性的努力是绝对排斥作为非理性之极致的疯癫体验的。福柯关于古典时期的疯癫体验的描述正是从评述笛卡尔开始的:“在怀疑的进路上”,除“梦想与全部谬误形式”之外,笛卡尔还“遇到了疯癫”,他极力避开它们,但“不像绕过梦想和谬误的或然性那样避开疯癫的危险”。[3]这一情形在那种只讲“理”而不言“情”的氛围中是不难理解的:“在怀疑的经济学中,一方面是疯癫,另一方面是梦想和谬误,它们之间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平衡。相对于真理和追求真理的人来说,它们的处境是不同的,梦和幻觉将在真理的结构本身中获得克服,而疯癫却受到进行怀疑的主体的排斥。”[4]
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或许会暂时受到感觉和梦幻的纷扰从而犯错,但它绝对不可能发疯。事实上,在由理性绝对主宰的世界中,疯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他在知识王国中也不可能有任何位置。在长篇大论地描述和分析疯癫体验在古典时代受到的彻底排斥后,福柯以狄德罗塑造的“拉摩的侄子”为开端引出了“现代疯癫史”,展示疯子的“现代形象”。“在怀疑涉及到他的各种主要危险的时刻,笛卡尔意识到他不可能是疯子”,而“拉摩的侄子则完全知道他自己是疯子”。[5]
“拉摩的侄子”代表了疯癫的尽管脆弱但初步的自觉:其存在是完全显而易见的,但18世纪并没有觉察到。福柯表示,虽然“18世纪不可能准确地理解《拉摩的侄子》透露的意义”,即“谵狂”在“疯癫的核心”中获得的“新的意义”,但“疯癫在现代世界里的命运,在此奇特地获得了预示,而且差不多已经开始了”。[6]这就表明出现了针对笛卡尔主义的反叛姿态。古典思想以怀疑为开端,最终获得的是确定性的观念,但现代思想放弃了对明证性的追求。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人鱼(继笼中谜)
- 嗯,重新写了一篇
- 0.1万字1年前
- 无聊的时候写写(不想看别看)
- 内容很杂,不喜勿喷
- 1.7万字1年前
- 变成男人去救世
- 兽人、羽人、鲛人…没带脑子,想哪儿是哪儿,大女主,全文女主最大。
- 7.3万字1年前
- 兽世:不按套路出牌的我在兽世乐逍遥
- 兽世穿越,无女主,双男主,不喜勿喷各种原因这本书大概是太监了,辜负了大家期望实在抱歉。
- 2.6万字1年前
- 魔法俏佳人所忘皆遗憾
- 魔法仙界全部人被卡罗玛修改记忆(除了仙灵组),蕾儿被追杀
- 2.4万字1年前
- 梦醒精灵起舞
- 梦一次一次的轮回,蓝诺朝着天大喊:“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里啊!我快要疯了!”梦里一道声音响起,蓝诺努力地睁开眼睛,却是一片黑暗,只听见一句:“......
- 10.3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