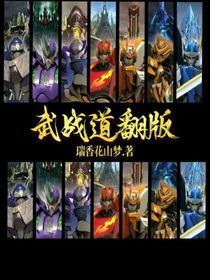游牧式统一:吉尔德勒兹论主权的本质(三) (4-4)
如果主权逻辑依赖于将多重性还原为统一性这一非常有问题的现象,那么主权权力的争夺就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统一性来抵制这种操作。至少我们必须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统一性之间划出政治区别。虽然从德勒兹的角度来看,想象和追求一个脱离统一性的世界、一个服从于多重性倾向的世界的可能性的想法是荒谬的。德勒兹认为,与自然界的统一相比,多重性倾向具有更大的力量和重要性,他认为多重性是人类政治的根源,但他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多重性只能在反对统一概念和通过统一概念的变换中来表达。真正的德勒兹式政治理论不能以多元的名义向统一性宣战。对德勒兹关于自然和政治中多元和统一关系的二元论理解是站不住脚的,那些以这种方式代表他的作品的批评家和爱好者都是大错特错的。“你问我是否相信游牧民族”,德勒兹曾回应一位批评家。“是的,我相信。成吉思汗不容小觑。他会死而复生吗?我不知道,但如果他会,那将是以其他形式复活的”(德勒兹 2002:260-1)。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尽管人类种族的本质统一性越来越成为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军事力量和暴力的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持续抵抗西方、极端自由、普遍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成的全球公理的实际形式问题却变得更加紧迫。存在着与西方世界公理相悖并与之对立的民族,这仍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事实。个别民族继续拒绝西方现代性的公理,积极选择以无视霸权全球秩序的监管要求的方式建立自己。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德勒兹的游牧主义哲学将与世界政治理论家产生共鸣,他们既不认为主权是理所当然的,也不相信其毁灭的天真乌托邦的可能。
结论
我读德勒兹的著作时,并非因为建构主义立场的作用是谴责自然话语在主权实践和理论合法化中的作用,将国际关系中已经本质化的建构主义立场僵化,而是探究了如何重新思考自然。在重新思考自然的过程中,在重新思考自然的过程中,尤其是如何重新概念化多重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以便重新评价后者,以支持那些政治能力取决于其能力的运动和人民,不是贬低统一性的概念,而是建立统一性的概念。仅仅试图谴责概念,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政治和哲学的双重问题是如何通过为概念注入新生命来重新发明它们(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9:15-34)。当通过更恰当的德勒兹方法论进行探究时,如何重新发明主权问题的问题不是如何拒绝关于自然的话语,因为它是构建自然的可能性的强大条件,所以应该是如何拒绝自然话语的问题。 重新思考构成它的统一性和多重性之间的关系。 一旦我们不仅认识到主权的自然性主张的偶然性,而且认识到统一性与多重性倾向之间的斗争问题的解决方式的偶然性,我们就为自己创造了建立不同的主权的能力。 关于自然的这两个基本方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讨论。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组织统一的愿望在有影响力的政治斗争话语中变得越来越病态。要反对日益全球化的禁令,即放弃对统一的渴望,重新思考政治作为多重性再生产的实践,就需要一个能够将自己视为由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构成的政治主体。政治主体的政治在于它能够将其多重性倾向与将自身生产为既定统一体的必要性结合起来。正如德勒兹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与国际政治理论中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之间的脱节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距离概念化这样的主体和实践这样的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