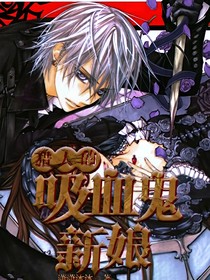虚无之上(二) (5-2)
我们继续囿于“相关性”的特点是,我们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将主体性与存在分开。所有对(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的等等)主体的批判都没有把我们从主体性(以理性、本能、权力意志、欲望等形式)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思辨唯物主义包括这样一个论点:可以而且必须能思考绝对的非主体性——因为它是所有思想的所在。因此,正是相对于这种绝对非主观的、被把握的事物——散布到最遥远星系的巨大物质性的死物——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存在的方向。
卡根·卡维西:正如有的生物即便没有氧气也能活下去,也有的生物无需概念也能思考;这些生物占大多数。但是,紧紧抓住概念的绳索,能够进入那些没有思想的时代的思想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在这里,概念最终是作为一种手段来瞥见独立于思想的绝对。你说这个绝对是超混沌的时间,通过你的概念和证明,你引导我们看到这个超混沌,你把这种看到的方式称为 “推理直觉”(dianoetic intuition)。我猜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定义推理直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直觉的概念与康德的感性直觉不同。通过推理直觉,我们可以把超混沌时间的深度想象成对应于不同类型的现实的层次。我想知道,某种“审美经验”是否伴随着这种对超混沌时间的推理直觉。根据康德的说法,数学上的崇高产生于我们无法将空间中的巨大尺寸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现在,由于推理直觉,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超混沌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巨大深度,而我们可以想象的异质层次不能构成一个整体。我可以想象,在过去,有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自然规律,因而有不同的实在;我也可以为未来想象这种多样性。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深度的超混沌时间,尽管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但这一事实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快乐的升华。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经验。但我想知道你会如何考虑你的思辨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审美方面。
甘丹·梅亚苏:严格来说,对超混沌有一个明智的或想象的直觉是不可能的。例如,我想说的是,认为超混沌可能产生的可能数量超过了所有确定的无限性,只能通过康托尔式的无限性来把握它,而康托尔式的无限性是由越来越大的基数组成的无限连续,看不到尽头。虽然我谈的是智力直觉,但我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直接接触到永恒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冲击着每一个具有这种混沌力量的实体。因为任何事实,无论是感知到的还是想到的,都不仅以其特质给予我们——一个冬天的夜晚,一条被半月照亮的雪道,而且还以一个事实,即它像一个永久的峡谷一样环绕着它,它是建立在一无所有之上的。你可以通过复杂的原因和自然法则来解释这样一个场景的所有元素,但你不能通过一个原因和一个终极规律来解释这些规律和原因。在任何时候,一切都被赋予了缺乏任何存在的理由,即使任何终极理由的这种虚无被“次要理由”所掩盖,即作为解释的相对原则的原因和规律都围绕着它。
因此,智力上的直觉是对形而上学话语和宗教信仰的无法把握的东西的直接把握,以解释每件事情的非理性和非必然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直觉:它是对围绕着现实的每一个碎片的无理性的直接的、非话语性的理解(能思直觉,不是推理直觉)。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超混沌看作是一种无垠的鸿沟,它有时会“陷入”自身,以至于使生成它的东西崩溃,以支持其他实在,也许是超乎寻常的其他实在(物质中的生命,生命中的思想)。它是一种无限的创造力量,不是通过像形而上学的神那样的无限完美,而是进入一个无与伦比的虚无,它的每一次虚无的痉挛都能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这是一种(混沌的)无中生有爆发,它不是(神圣的)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其根本的对立面——它是永恒的,而不是超越的。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镜中蝶笙
- 杀戮游戏悄然诞生,游走在生命的边缘,斩断荆棘将利刃刺向神明……(分数多以be为结局,注意避雷哦)
- 0.8万字1个月前
- 永生的秘密
- 她说“我不要永生,我也不要回去,我只等妹妹喊我一声姐姐。”他说“永生不可怕,我会陪你一块待着永生界,哪怕永远在那里,我都会陪你,我会和你一起......
- 15.7万字4周前
- 拾锦—贰
- 一个人若享受了孤独,便不觉得孤独。可你为何偏偏出现在我身边?——锦年因为你值得。——韩澈我阿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可是她不爱笑。——苏柒殿......
- 11.5万字4周前
- 我叫小白,没有姓
- 小白,一个没有根的物种,本以为自己是平凡普通没人爱的宅女,哪成想,自己居然是神仙!还没适应自己的神仙身份,又说是她妖精!她到底是谁啊?!等等......
- 16.6万字4周前
- 猎人的吸血鬼新娘
- 当吸血鬼女王遇上吸血鬼猎手,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三生三世,纠缠不断,爱恨情仇,谁是谁的人?
- 1.9万字4周前
- 妖魂童子
- 在中世纪灭巫之战中,巫师、炼金术士、灵媒师等拥有异能之人潜伏于地下,成立了名为暗星的组织,彼此协手走过了黑暗时代,直至今日依旧在保卫着那些不......
- 16.4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