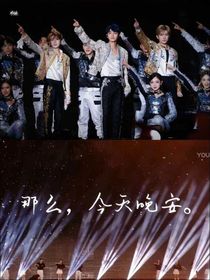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一 (5-5)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从来不问如果。这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论视野(horizon)的范围,超出了他的基本概念(concepts)所界定的领域的范围。他一方面接受观察到的实在,另一方面接受他用那种普遍的组合产生的可能性:当他遇到一个实在时,对他来说,全部难题(problem)在于从这个组合游戏(the play of the combinatory)[12]出发,构筑这个实在的可能性。然而,使它变得清晰易懂,并不是通过生产一种存在的实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生产其必然性的概念(concept)(这种特殊的可能性,不是其他的可能性)来实现的。要理解一个真实的现象,我要说,不是生产可能性的概念(那仍然是古典的哲学意识形态,是我在《读〈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谴责的典型合法操作);相反,这是生产必然性的概念(concept)的事情。列维-斯特劳斯的形式主义是错误的形式主义,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与这个非常明确的点联系起来:列维-斯特劳斯把可能性的形式主义当作必然性的形式主义。
2.我刚才所说的列维-斯特劳斯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也适用于他对意识形态的分析,这种方式会更令人信服。然而我知道,一旦涉及到意识形态和列维-斯特劳斯对它的分析时,一些会同意我所说的亲属关系结构的人,就会沉默起来。因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形式主义似乎更适合分析神话,因为列维-斯特劳斯似乎不会像在亲属关系结构的情况下那样,去把神话搞混。如果他不知道亲属关系结构是作为生产关系发挥其功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显示出可以观察的结构,一旦生产关系不再与亲属关系结构合并起来,这些结构在我们的社会中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如果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结构的性质和作用上犯了错——另一方面,他对神话的看法似乎是对的,因为他认为神话就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他自己说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他似乎已经为他准备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对象是真实的,并且已经为它找到了对的名字。不幸的是,名字本身(ipso facto)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因为列维-斯特劳斯不知道意识形态是什么(尽管他说他正在与意识形态打交道),因为他不知道在生产方式的复杂连接(articulation)中,而且更确切地说(a fortiori),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几种生产方式的组合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层面是什么,他求助于——而不是给予我们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就是说,而不是生产它们的不同形式的必然性的概念——在亲属关系结构的情况下起作用的进程(procedure)和意识形态诱惑(temptations)(好得很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他再次经历了同样的“理论”进程。他将意识形态形式追溯到在组合的(及其古典的、最终是双重的进程)基础上被构筑的可能性;组合本身反过来又可以追溯到人类精神的“机能”(faculty),就好像这种组合就是它的效果之一,或者,当希望在他内心消逝(或再次开始激荡)时,他就会追溯到大脑!他没有退缩,而是打着错误的形式主义的旗帜下前进(又一次是可能性,一种从根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主义)。要么相同的形式被确认(identified)为与其他存在形式(借助组合的进程的“美德”),亲属关系的或经济的或语言交流的形式同源(homologous);要么它们最终被确定为某些“经济”因素(“生活方式”、“地理条件”等等),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些因素相当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经济层面的理论,而他对生产方式的概念存在一无所知。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的“症结”(sticking-point)在于,他绝对不能解释在给定的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特定形式的意识形态存在的真正多样性:他只考虑可能性,一旦他生产了可能性的概念(concept),他就假设他不再需要担心必然性的概念,他对此无动于衷。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虽然她是绿茶,但她茶的是我诶
- 0.2万字1个月前
- 十载梦回
- 十年之后,子弹正中眉心,将“我”带到他们身边(仅供娱乐,自行代入)
- 7.2万字4周前
- 十二星:春心付海棠
- 白鸟告诉我你的踪迹说看到了污浊的白我想,你应该是纯洁的不是白纸,不是雪应当是云,随心但捉摸不透的云请盯着我的眼睛,看我那清澈的双眸只有你一人......
- 0.8万字4周前
- 女配也想修仙
- *原创**抄袭必究*顾汐月穿书了,还是个无恶不作的王者型女配,各种挑衅女主,最后被扔进蛇窟里自生自灭了。她微咧嘴角,谁说女配没有资格修仙,她......
- 7.3万字4周前
- 红晕1
- 吸血鬼和女孩
- 7.1万字4周前
- 图渊
- “图渊,你真好看!”“嗯。”“嘿嘿,图渊,介意娶个媳妇不?”“嗯?”……曾经,洛葵的死党放下手上的书,神秘兮兮的问她:“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龙......
- 10.3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