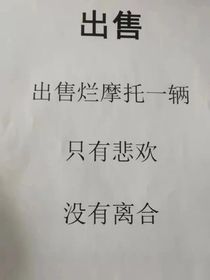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一 (5-2)
列维-斯特劳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产方式。他不懂马克思。这种误认(ignorance)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他想象出了他所论述的“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ies)这个概念(实质上,在许多情况下,他都只是在论述“起源”originally——“起源”意味着当他在谈论非原始社会non-primitive societies时,他就只是将关于原始社会之工作的范畴和后果转移到非原始社会上,这是十分清楚的)——这种无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他在一种古典的民族学的范畴的基础上,论述想象的“原始社会”的现象,但没有批判这些范畴。民族学的偏见,从而民族学的意识形态的根本来源,实际上存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原始”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它和除它之外的社会区分开,并阻碍我们使用这样一种范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种范畴使我们能够思考其他社会。实际上,在“原始社会”这种民族学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发现,除了这些社会的性质和它们特有现象的不可简化的特殊性的概念(notion)之外,还有一种概念,即这些社会不仅在相对的意义上,而且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原始的:在所谓“原始社会”里,原始这个词对民族学意识形态家和列维-斯特劳斯(见《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以及他在[法兰西][5]学院里的讲演)来说总是或多或少意味着起源。原始社会不仅是原始的,它也同样是起源的:它们以经验的、可感知的形式容纳着真理,这种真理,在我们的非原始的、复杂的(complex)、文明的……社会中,被掩盖和异化(alienated)了。这是卢梭的古老神话(列维-斯特劳斯经常提到他,从他那里只拿来了这个神话,尽管在卢梭那里有许多可以说很天才的其他东西),却被民族学家罪恶地(by the bad conscience)复活,这些殖民者的儿子为了减轻这种罪恶感,就声称原始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中的“人类”,然后和他们交起朋友来(看看列维-斯特劳斯对他和原始人之间突然出现的友谊的回忆)。我知道这一切看起来可能很“容易”,但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在于去看待这个“容易”的后果(consequences)。
列维-斯特劳斯使自己的事情变得容易的基本后果——通过省略了质疑在民族学的意识形态中非常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反过来屈服于它——就是阻碍他去处理马克思那些话的本质。如果我们真正去阅读和聆听马克思的话,那我们就别无选择,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
1.不存在所谓的原始社会(这不是一个科学概念concept);然而,我们可以用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s)[6](这是一个科学概念)来暂时称呼原始,它的意义完全没有被起源(origin)的理念所污染(纯粹的、新生的文明,透明的、纯粹的、消极的人类社会关系的真理等等);
2.像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一个原始的社会形态由一些只能与生产方式概念联系起来才能被思考的结构组成,并且有一些从属概念(subordinate concept)去暗示和容纳它(就是说,一种生产方式存在于一种经济基础、一种法律-政治上层建筑、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里面);
3.像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一个原始的社会形态具备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至少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组合的后果,其中一种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而其他的生产方式从属它(比如说,打猎和养牛,打猎和耕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打猎和采集,采集与钓鱼,或者耕作与采集,以及打猎或养牛,等等)[7];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精彩小片场
- 一些作者一些未写作出的书,里面的有趣片段。还有一些是与作者的书无关的,但那些是作者想的一些优美画面。
- 2.5万字1个月前
- 快穿,清冷男主太爱
- 傅云被我灼灼的目光盯得有些发毛,他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你有什么毛病?怎么突然发起脾气来了?”我的心情很复杂,但还是尽力保持着平静......
- 1.1万字1个月前
- 梦中梦商店
- 马戏团文学
- 2.5万字4周前
- gb小合集
- gb女上第四爱雷点勿自产粮短篇文
- 1.2万字4周前
- 人间启明星
- 【静澜文社】搬家啦不在这里写噜星光点缀夜河无需月光照耀你是独属于我的星光我的启明星劳埃德单人向请自行带入
- 5.1万字4周前
- 腹黑妖仙古灵精怪
- 〖幽殇文学社〗她,似妖非妖,似仙非仙,傲世。众人皆知她“狂”,狂又如何?其月,尤见身袭蓝衣,吾言解刃。遇墨,尤闻淡淡酒味,浅浅笑意。
- 26.3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