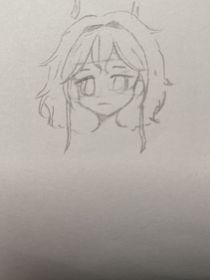萨缪尔森经济理论与数学(一) (5-5)
比较像法语这样的语言与德语、英语或中文会有些困难。我们可以承认,一种语言中的任何命题都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这与一种语言在某种特定用途上是否本质上更方便的心理问题无关。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法语是一种非常清晰的语言,而德语则非常晦涩。这一点由一个故事来说明:据说黑格尔直到读了法语译本后才真正理解他的哲学!
我不知道这是否有道理。在我看来,用德语写的Böhm-Bawerk或Wicksell和用英语写的一样直截了当;而我发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或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则用任何语言都很难理解。我怀疑某些文化会发展出特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中,一个很流行的问题是:利率或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在回答了这个定性问题之后,利率或价格比率的定量水平就可以解决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无效的方法。但我不能把这归咎于德语。
有趣的是,门格尔就这个问题给瓦尔拉斯写了一封信。正如贾菲教授(Professor Jaffe)那篇有趣的文章(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6)所提到的那样,门格尔说,数学对于某些描述的目的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它不能让你抓住现象的本质。我真希望我认为数学语言有某种特殊的能力,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定性本质的伪问题上引开。我不像门格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培根和牛顿方法。在许多经验领域中,转换成数学符号似乎没有任何优势。也许免疫学(immunology)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我被告知,没有一个疾病的治疗方法——如牛痘接种、白喉预防接种、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的使用等等——不是通过最粗略的经验主义发现的,并且偶然因素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平实方法显示出比牛顿的高深方法更大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我相信许多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领域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很可能许多这样的领域将永远停留在这一阶段。
帕累托(Pareto)认为社会学属于这一类型。但很奇怪的是,他接着论证说,数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表示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现象。我认为我们必须对此持保留态度。如果类比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物理系统能提醒我们单方面因果理论的危险性,那么这种类比是有价值的。但是,在数学概念提醒我们一切事物都相互依赖之后,它们可能不会增加太多额外的价值——除非可以根据事实做出一些特殊的假设。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精华小故事
- 很多的故事汇合
- 0.2万字8个月前
- 无限流:疯批美人她十恶不赦
- 【已签约,签约时间为2024.8.29】【无限流/双女主/双强/金手指/微悬疑】 池漾意外进入了无限流副本当中,开局不但获得了金手指,还被......
- 7.7万字8个月前
- 小说(合)
- 0.1万字8个月前
- 我画画进步史
- 0.0万字8个月前
- 我的师父谱尼大人
- (完结)《我的师父谱尼大人》就是冰倾儿与谱尼是师徒关系,日久生情谱尼发现自己喜欢冰倾儿,但是冰倾儿可是个万年直女完全看不出来谱尼喜欢自己,冰......
- 12.0万字8个月前
- 朝朝倾目
- 【已签约‖禁抄袭】(欢脱文+反穿反+女强+甜中带虐)不可一世的大魔王穿越后,转身一变娇弱“大白兔”谈情说爱,虐爆渣渣,变身富豪,一个不落。大......
- 7.2万字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