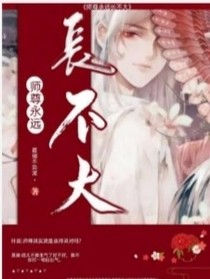对中囯的哲学中的两个教条的批判(二) (5-2)
我们认为,反对第二个教条的有力论据是:在精心设计一个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在和未来所有的问题时,设计者不可能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预测到未来人类活动中会发生什么。他没有办法知道在体系构造完成以后,有哪些问题会被提出来,因为现在和过去会有很大的不同,未来和现在会有更大的不同,新的事件总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发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者无法预测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他/她无法将这些新问题的解决方案纳入她/他的系统。预测未来问题的不可能性是基于预测人类未来的不可能性。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其《历史主义的贫困》(Popper 1957)一书中所论述的,有四个原因使我们无法预测人类的未来:
首先,对整个社会历史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构成这种描述的特征的清单将是无限的。如果我们不能知道人类的全部现状,那么我们也就不能知道人类的未来。波普尔写道:“如果我们想研究一个事物,我们必然要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连最小的整块都不可能被这样描述,因为所有的描述都必然是选择性的。”(Popper 1957, p. 77)
第二,人类历史是一个单一的独特事件。因此,对过去的了解不一定能帮助人们了解未来。(Popper 1957, p. 108)
第三,人类个体的行动或反应永远无法被确定地预测,因此未来也无法预测。“人这一因素是社会生活和所有社会机构中最终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事实上,这是最终不能被制度完全控制的因素(正如斯宾诺莎首先看到的)”。(Popper 1957, p. 158)
第四,当历史的进程部分取决于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时,我们不可能知道历史的未来进程,因为我们无法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无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在上个世纪,没有人想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在这个世纪,没有人预料到基因编辑和合成基因组的发明,也没有人预料到人工智能软件的出现,如击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Deep Blue或赢得围棋大师李世石的AlphaGo。假设这个普遍性体系的设计者生活在基因编辑技术被发明之前,设计者也无法预测这项技术带来的任何伦理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基因编辑中的体外胎儿研究?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对体细胞基因编辑进行临床试验,并将其视为普通疗法?我们应该进行可遗传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吗?对后代的健康和生命将受到可遗传基因编辑的影响,我们是否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福祉?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功能,使之超越我们这一物种所拥有的功能?还有:我们是否应该对非人类生物进行基因编辑,包括消除有害物种,如传播疟疾和登革热的埃及伊蚊;恢复被淘汰的物种,如猛犸象;或产生传说中的物种,如独角兽?等等。如果设计者对这些伦理问题一无所知,他或她就无法将这些伦理问题的解决纳入她或他的体系中。
2.2 可能的反驳理由
一种观点可能会声称,在普通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些现有的理论、原则或规则来解决。这是真的,但这个问题必须是一个常规问题。请考虑一下下面的推论:
(1) 所有患有肺炎的病人,如果没有任何超敏反应或免疫反应和其他并发症,都应该使用青霉素处方;
(2) 患者A患有肺炎,没有任何过敏或免疫反应和其他并发症;
(3) 那么患者A应使用青霉素。
在这个常规案例中,没有任何伦理上的困难,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从现有的规则中推断出医生应该做什么。
然而,考虑另一种情况。在一个更重要的例子中,演绎法已经不起作用了。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尝血
- 沫沫莫莫
- 0.5万字9个月前
- 洪荒封神:天尊,谈个恋爱呗
- 洪荒传说,元始天尊小心眼,精于算计,心狠手辣,连亲兄弟都不放过。凛谕和元始天尊成了邻居,一次意外压倒了他,从此被缠上,再也无法脱身。元始天尊......
- 66.5万字9个月前
- 当alpha穿越到异世界的二三事
- 江月从21世纪娇滴滴的白幼瘦变成星际社会的Alpha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适应身份的转变江月和她的室友们非常倒霉穿越到异世界遇到了各方大佬揍......
- 31.2万字9个月前
- 甜宠兽世:快把兽夫带回家
- 段夏月因被组织追杀,意外来到了兽世,兽世虽然穷,这资源还是不错的,还别说,这帅哥真多啊。霸道兽王来相争,各路兽王都拜倒在段夏月的石榴裙下还有......
- 9.6万字9个月前
- 师尊永远长不大
- 1.叶寂前世杀了他师尊后一朝重生,本想离开师尊(莫凌)后带着夜淋离开寻找变强的办法好保护他,但跟在他身边的一直是自己憎恶已久的师尊,久而久之......
- 7.7万字9个月前
-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 一个南瓜的爆笑仙侠之旅
- 4.5万字9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