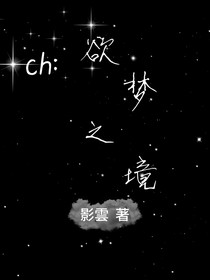【数学与哲学翻译】Peter Smith论数学 (7-7)
但正如我们刚才注意到的,从历史上看,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此,虽然逻辑主义(Imre提到过)和希尔伯特的复杂形式主义是保守的主义,且它们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些方案,来坚持“经典数学没有毛病,不需要改动”这一主张,但这些主义的立场却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些其他的、根本性的、批判性的主义。这些包括著名的布劳威尔直觉主义和魏尔的直谓主义。批评者认为,19世纪末的经典数学在陷入“抽象废话”时已经过度扩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发现集合论和其他悖论时出现了基础危机),而为了摆脱困境,我们需要坚持更具构造性/直谓性的推理风格,认识到数学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建构(你也可能会认为这与我们如何获取数学知识有关)。
这个故事目前我讲得还是很粗糙,不过我们无法在这里进一步跟进这些争论了。然而,作为一个简单的历史概述,发生的事情是,就数学实践而言,保守的经典实在论者获胜了。例如,直谓分析在数学大厦的一个小房间里幸存下来,那里的从业者仍然喜欢炫耀他们可以单腿跳多远,或者说他们可以单手绑在背后跳多远(“抽象废话”的爱好者就会这么描述他们的工作,借用Thomas的说法)。然而还是要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事实证明,对科学来说,直谓分析实际上似乎已经完全够用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外部的、功利性的理由去做经典主义数学)。但经典实在论者的胜利并不是一个概念上有充分理由的哲学性胜利——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胜利,但这绝对不是其中之一。概念上的争论一直有持续,但希尔伯特和其他人的政治权威足以说服大多数数学家,他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所以他们就没有改变。(译者注:此处作者指的是数学史上著名的Brouwer-Hilbert事件,该事件由两人的数学哲学观念争论而生,继而上升到具体的职业生计纠纷,最终Hilbert将Brouwer从Mathematische Annalen编辑委员会除名)
然而——现在我要更加幻想一些,但我希望不会太过分——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在某个孪生地球上事情发展得有所不同。在那里,数学家的内部文化(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哲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发展与我们不同,以至于低承诺的方法变得特别受重视,而构造主义者/直谓主义者们占据了大厦的主要房间,给他们的学生发放奖学金。而那些抽象废话的爱好者们被放逐到阁楼上,去玩他们的野生集合论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娱乐数学系”里。或者如果你觉得我们无法想象这种情况,又为什么无法想象呢?
我们还有许多能讨论的内容。但也许,只是也许,数学家在对哲学家不屑一顾之前,应该偶尔反思一下,我们的数学实践是否真的没有与一些深层次的、广泛的大图景的假设紧密相连,而这些假设是值得挑战的。如果,正如Imre在开头所说的,数学家倾向于是柏拉图主义者,那完全有可能这种“主义”的站队并不是一个脱离数学实践、无所事事的哲学花瓶,而是在产生一些确确实实需要被认识和反思的切实影响。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异世界之许下不言弃的山盟海誓
- “虚假的神明,迷乱世人的眼睛”“他是废墟唯一的信徒”原创女频西幻文有cp食用愉快
- 0.2万字1个月前
- ch:欲梦之境
- 一次意外,在联合国开会的众人进入了一个名为欲梦之境的地方……(私设勿喷!ooc致歉)(本人才入ch圈不久,文笔也一般,多多包涵)(住校生,更......
- 0.4万字4周前
- 猫武士火星疯了
- 这是一篇小说,希望你们能鼓励一下我
- 0.2万字4周前
- 修仙计划
- 被神仙选中和他一块做任务,看在能成神仙的份上洛璃同意,只是那个老头子怎么总是闯进她和搭档的空间来。
- 10.0万字4周前
- 古风图片铺子一一青街陌路
- 图片和故事有的来自于网络,喜欢的自己拿走。
- 1.9万字4周前
- 末世之神明的游戏
- 突然的末世,猝不及防,觉醒异能,也不能完全走向人生巅峰,异兽一个接的一个,哪才是人类的净土……
- 10.4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