йӣҫиө·йӣҒй—ЁпјҢеҰ–ж°”йҡҗзҺ°
йқ’еҙ–еұұзҡ„еІҒжңҲйқҷж°ҙжөҒж·ұпјҢиҪ¬зңјеҸҲжҳҜеҚҒиҪҪгҖӮйҳҝзҰҫеңЁзҒөи„үж»Ӣе…»дёӢпјҢе®№йўңе§Ӣз»ҲеҒңз•ҷеңЁиҖҢз«Ӣд№Ӣе№ҙзҡ„жЁЎж ·пјҢзңүзңјй—ҙзҡ„жё©е©үдёҺиӢұж°”дәӨиһҚпјҢжӣҙжҳҫйҹөе‘ігҖӮеўЁжёҠеҲҷж„ҲеҸ‘жё©ж¶ҰпјҢе‘Ёиә«зҒөж°”жөҒиҪ¬иҮӘеҰӮпјҢеҒ¶е°”еӮ¬еҠЁеҠӣйҮҸж—¶пјҢзңүй—ҙй№ҝеҚ°йҮ‘е…үжөҒиҪ¬пјҢеҚҙеҶҚж— еҚҠеҲҶжҚҹиҖ—д№ӢжҖҒгҖӮ
иҝҷж—Ҙжё…жҷЁпјҢйҳҝзҰҫз…®иҢ¶ж—¶пјҢеҝҪ然жңӣзқҖйӣҒй—Ёе…ізҡ„ж–№еҗ‘еҮәзҘһгҖӮеўЁжёҠи§ҒеҘ№зҘһиүІжҖ…然пјҢж”ҫдёӢжүӢдёӯд№ҰеҚ·иө°иҝҮеҺ»пјҡвҖңеңЁжғід»Җд№ҲпјҹвҖқ
вҖңжғіиө·йӣҒй—Ёе…ідәҶгҖӮвҖқйҳҝзҰҫиҪ»еЈ°йҒ“пјҢвҖңдёҚзҹҘйӮЈдәӣиҖҒйғЁдёӢиҝ‘еҶөеҰӮдҪ•пјҢеҹҺеўҷдёҠзҡ„еҶӣж——пјҢжҳҜеҗҰиҝҳеҰӮеҪ“е№ҙйӮЈиҲ¬йІңзәўгҖӮвҖқ
еўЁжёҠжҸЎдҪҸеҘ№зҡ„жүӢпјҢжҢҮе°–жё©ж¶ҰпјҡвҖңиӢҘжғіеӣһеҺ»зңӢзңӢпјҢжҲ‘们дҫҝеҺ»гҖӮеҰӮд»ҠжҲ‘йӯӮзҒөзЁіеӣәпјҢеҸҜжҗәдҪ иҝңиЎҢдёғж—ҘпјҢдёғж—Ҙд№ӢеҶ…пјҢзҒөи„үд№ӢеҠӣд»ҚиғҪжҠӨжҲ‘дёҚж•ЈгҖӮвҖқ
йҳҝзҰҫзңјдёӯдёҖдә®пјҢйҡҸеҚіеҸҲжңүдәӣзҠ№иұ«пјҡвҖңдјҡдёҚдјҡеӨӘеҶ’йҷ©пјҹвҖқ
вҖңж— еҰЁгҖӮвҖқеўЁжёҠиҪ»з¬‘пјҢвҖңеҪ“е№ҙдҪ е®ҲйӣҒй—Ёе…іжҠӨжҲ‘пјҢеҰӮд»ҠжҚўжҲ‘йҷӘдҪ ж•…ең°йҮҚжёёгҖӮвҖқ
дёүж—ҘеҗҺпјҢдёӨдәәеҢ–дҪңеҜ»еёёеӨ«еҰ»жЁЎж ·пјҢиёҸдёҠеүҚеҫҖйӣҒй—Ёе…ізҡ„и·ҜгҖӮдёҖи·ҜеҚ—дёӢпјҢжҳ”ж—ҘиҚ’еҺҹе·ІиҰҶйқ’иҚүпјҢжқ‘иҗҪзӮҠзғҹиў…иў…пјҢеҶҚж— жҲҳд№ұз—•иҝ№гҖӮжҠөиҫҫйӣҒй—Ёе…іж—¶пјҢеҹҺеўҷдҫқж—§е·ҚеіЁпјҢеҸӘжҳҜеҹҺй—ЁеҸЈеӨҡдәҶеҮ дҪҚй”ҰиЎЈдҫҚеҚ«пјҢзҘһиүІиӯҰжғ•ең°зӣҳжҹҘеҫҖжқҘиЎҢдәәгҖӮ
йҳҝзҰҫжӯЈи§үеҘҮжҖӘпјҢиә«еҗҺеҝҪз„¶дј жқҘдёҖеЈ°иӢҚиҖҒзҡ„е‘је”ӨпјҡвҖңиҝҷдҪҚеӨ«дәәвҖҰвҖҰжӮЁеҸҜжҳҜйҳҝзҰҫе°ҶеҶӣпјҹвҖқ
еҘ№иҪ¬еӨҙпјҢи§ҒеҪ“е№ҙзҡ„еүҜе°ҶиҖҒеј жӢ„зқҖжӢҗжқ–пјҢеӨҙеҸ‘е…ЁзҷҪпјҢиә«еҪўдҪқеҒ»пјҢеҸӘжҳҜзңјзҘһдҫқж—§й”җеҲ©гҖӮеҸҜеҪ“иҖҒеј зҡ„зӣ®е…үжү«иҝҮеўЁжёҠж—¶пјҢжө‘жөҠзҡ„зңјзқӣйӘӨ然зһӘеӨ§пјҢиёүи·„зқҖеҗҺйҖҖеҚҠжӯҘпјҢеЈ°йҹіеҸ‘йўӨпјҡвҖңжӮЁвҖҰвҖҰжӮЁжҳҜеўЁжёҠе…Ҳз”ҹпјҹпјҒеҪ“е№ҙжӮЁдёҚжҳҜвҖҰвҖҰвҖқ
д»–иҜқжңӘиҜҙе®ҢпјҢдҫҝзҢӣең°жҚӮдҪҸеҳҙпјҢиӯҰжғ•ең°зңӢеҗ‘еӣӣе‘ЁпјҢжӢүзқҖдёӨдәәеҫҖеғ»йқҷе··еј„иө°пјҡвҖңжӯӨең°дёҚдҫҝиҜҙиҜқпјҢйҡҸжҲ‘жқҘпјҒвҖқ
еҲ°иҖҒеј е®¶дёӯпјҢд»–е…ізҙ§йҷўй—ЁпјҢжүҚйўӨе·Қе·Қең°зңӢеҗ‘еўЁжёҠпјҡвҖңе…Ҳз”ҹеҪ“е№ҙйӯӮеҪ’еұұжө·пјҢеҰӮд»ҠжҖҺдјҡвҖҰвҖҰиҖҢдё”жӮЁиә«дёҠиҝҷж°”жҒҜвҖҰвҖҰиҷҪжё©е’ҢвҖҰвҖҰвҖқ
еўЁжёҠйў”йҰ–пјҢ并жңӘйҡҗзһ’пјҡвҖңжҲ‘жҳҜйқ’еҙ–еұұй№ҝиңҖз‘һе…ҪпјҢеҪ“е№ҙйӯӮзҒөеҸ—жҚҹжІүзқЎпјҢеҰӮд»ҠеҖҹйҳҝзҰҫжү§еҝөдёҺйқ’еҙ–зҒөи„үеҪ’жқҘгҖӮвҖқ
иҖҒеј еҖ’еҗёдёҖеҸЈеҮүж°”пјҢйҡҸеҚіжү‘йҖҡи·ӘдёӢпјҡвҖңе…Ҳз”ҹжҳҜз‘һе…ҪйҷҚдё–пјҢеҪ“е№ҙиҲҚиә«жҠӨе…іпјҢжҲ‘зӯүдёҮжӯ»йҡҫжҠҘпјҒвҖқ
вҖңеј еӨ§е“Ҙеҝ«иө·гҖӮвҖқйҳҝзҰҫиҝһеҝҷжү¶иө·д»–пјҢвҖңд»Ҡж—ҘеӣһжқҘпјҢеҸӘжҳҜжғізңӢзңӢеӨ§е®¶е®үеҘҪгҖӮвҖқ
иҖҒеј жҠ№дәҶжҠҠжіӘпјҢеҚҙеҝҪ然еҺӢдҪҺеЈ°йҹіпјҡвҖңе°ҶеҶӣжңүжүҖдёҚзҹҘпјҢиҝҷйӣҒй—Ёе…іеҰӮд»ҠзңӢзқҖеӨӘе№іпјҢе®һеҲҷжҡ—жөҒж¶ҢеҠЁгҖӮдёҠжңҲпјҢзҡҮж—Ҹзҡ„дёүзҡҮеӯҗеёҰзқҖдәІеҚ«й©»жүҺеңЁжӯӨпјҢиҜҙжҳҜе·ЎжҹҘиҫ№еўғпјҢеҸҜжҲ‘жҳЁеӨңе·ЎиЎ—ж—¶пјҢеҚҙеңЁд»–иҗҘеӨ–й—»еҲ°дәҶвҖҰвҖҰеҰ–ж°”гҖӮвҖқ
вҖңеҰ–ж°”пјҹвҖқеўЁжёҠзңүеі°еҫ®и№ҷпјҢзңүй—ҙй№ҝеҚ°й—ӘиҝҮдёҖдёқйҮ‘е…үпјҢвҖңжҳҜдҪ•з§ҚеҰ–ж°”пјҹвҖқ
вҖңиҜҙдёҚдёҠжқҘпјҢи…Ҙз”ңи…»дәәпјҢдёҚеғҸеҜ»еёёзІҫжҖӘпјҢеҖ’еғҸжҳҜвҖҰвҖҰдёҠеҸӨеҮ¶е…Ҫзҡ„ж®ӢжҒҜгҖӮвҖқиҖҒеј и„ёиүІеҮқйҮҚпјҢвҖңдёүзҡҮеӯҗиҝҷдәӣж—Ҙеӯҗйў‘з№ҒеҮәе…Ҙе…іеӨ–иҚ’еҺҹпјҢдјјеңЁеҜ»жүҫд»Җд№ҲпјҢжҲ‘жҖ•д»–жҳҜжғіе”ӨйҶ’еҪ“е№ҙйҘ•йӨ®зҡ„ж®ӢйӯӮпјҢжҗһеҮәд№ұеӯҗпјҒвҖқ
йҳҝзҰҫзҘһиүІдёҖеҮӣпјҢеҪ“е№ҙйҘ•йӨ®д№ӢзҘёзҡ„жғЁзғҲд»ҚеңЁзңјеүҚпјҡвҖңд»–дёәдҪ•иҰҒиҝҷд№ҲеҒҡпјҹвҖқ
вҖңеҗ¬й—»дёүзҡҮеӯҗеңЁжңқдёӯдәүеӮЁеӨұеҲ©пјҢжғіеҖҹеҮ¶е…Ҫд№ӢеҠӣйҖ еҠҝпјҢжҺҢжҺ§иҫ№е…іе…өжқғгҖӮвҖқиҖҒеј еҸ№йҒ“пјҢвҖңжҲ‘жң¬жғідёҠжҠҘжңқе»·пјҢеҸҜд»–жҳҜзҡҮж—Ҹе®—дәІпјҢжҲ‘иҝҷиҖҒйӘЁеӨҙдәәеҫ®иЁҖиҪ»пјҢжҖ•жҳҜжІЎејҖеҸЈе°ұиў«зҒӯеҸЈдәҶгҖӮвҖқ
еўЁжёҠжҢҮе°–иҪ»еҸ©жЎҢйқўпјҢзңјдёӯй—ӘиҝҮеҶ·е…үпјҡвҖңйҘ•йӨ®ж®ӢйӯӮиҷҪзҒӯпјҢдҪҶиӢҘжңүдәәд»ҘзІҫиЎҖеј•еҠЁпјҢзҡ„зЎ®еҸҜиғҪиҒҡз…һйҮҚз”ҹгҖӮжӯӨдәӢдёҚеҸҜеӨ§ж„ҸгҖӮвҖқ
йҳҝзҰҫзңӢеҗ‘еўЁжёҠпјҢзңјзҘһеқҡе®ҡпјҡвҖңе…Ҳз”ҹпјҢжҲ‘们дёҚиғҪеқҗи§ҶдёҚз®ЎгҖӮйӣҒй—Ёе…іжҳҜдҪ жҲ‘з”ЁжҖ§е‘Ҫе®ҲдҪҸзҡ„ең°ж–№пјҢз»қдёҚиғҪеҶҚйҒӯзҘёд№ұгҖӮвҖқ
еўЁжёҠжҸЎдҪҸеҘ№зҡ„жүӢпјҢжё©еЈ°йҒ“пјҡвҖңдҪ ж”ҫеҝғпјҢжҲ‘иҷҪдёҚиғҪд№…зҰ»йқ’еҙ–еұұпјҢдҪҶдёғж—Ҙд№ӢеҶ…пјҢи¶іеӨҹи§ЈеҶіжӯӨдәӢгҖӮвҖқ
еҪ“жҷҡпјҢеўЁжёҠд»Ҙй№ҝиңҖд№ӢеҠӣйҡҗеҢҝиә«еҪўпјҢжҪңе…ҘдёүзҡҮеӯҗиҗҘдёӯгҖӮиҗҘеҶ…жһң然ејҘжј«зқҖж·Ўж·Ўзҡ„и…Ҙж°”пјҢеёҗдёӯжЎҲеҮ дёҠж‘ҶзқҖдёҖдёӘйқ’й“ңйјҺпјҢйјҺеҶ…зҮғзқҖй»‘йҰҷпјҢйҰҷзҒ°дёӯж··зқҖжҡ—зәўиүІзҡ„иЎҖжёҚвҖ”вҖ”з«ҹжҳҜжҙ»дәәзІҫиЎҖгҖӮ
еёҗеҗҺдј жқҘдёүзҡҮеӯҗзҡ„еЈ°йҹіпјҢеёҰзқҖйҳҙзӢ пјҡвҖңйҘ•йӨ®ж®ӢйӯӮдҪ•ж—¶иғҪиҒҡпјҹжң¬зҡҮеӯҗзӯүдёҚеҸҠдәҶпјҒвҖқ
вҖңж®ҝдёӢзЁҚе®үпјҢеҶҚжңүдёүж—ҘпјҢд»ҘзҷҫдәәжҖ§е‘Ҫдёәеј•пјҢе®ҡиғҪе”ӨеӣһеҮ¶е…Ҫж®ӢзҒөпјҒвҖқдёҖдёӘе°–з»Ҷзҡ„еЈ°йҹіеӣһеә”пјҢз«ҹжҳҜдёҖеҸӘеҢ–еҪўзҡ„зӢҗеҰ–гҖӮ
еўЁжёҠзңјдёӯйҮ‘е…үйӘӨзӣӣпјҢжӯЈж¬ІеҠЁжүӢпјҢеҚҙеҝҪи§үе‘Ёиә«зҒөж°”дёҖж»һвҖ”вҖ”дёүзҡҮеӯҗеёҗеӨ–еёғдәҶй”ҒзҒөйҳөпјҢз«ҹжҳҜдё“й—Ёй’ҲеҜ№зҘһе…Ҫзҡ„зҰҒеҲ¶гҖӮ
д»–йҖҖиҮіиҗҘеӨ–пјҢдёҺйҳҝзҰҫгҖҒиҖҒеј жұҮеҗҲпјҢжІүеЈ°йҒ“пјҡвҖңдёүзҡҮеӯҗеӢҫз»“еҰ–зү©пјҢд»Ҙжҙ»дәәзІҫиЎҖеј•йҘ•йӨ®ж®ӢйӯӮпјҢдёүж—ҘеҗҺдҫҝиҰҒеҠЁжүӢгҖӮеёҗеӨ–жңүй”ҒзҒөйҳөпјҢжҲ‘йңҖеҖҹйқ’еҙ–зҒөи„үд№ӢеҠӣз ҙйҳөпјҢдҪҶиҝҷдјҡиҖ—жҚҹдәӣи®ёжң¬жәҗпјҢдҪ еҸҜдјҡжӢ…еҝғпјҹвҖқ
йҳҝзҰҫж‘ҮеӨҙпјҢе°Ҷи…°й—ҙзҺүдҪ©пјҲеҪ“е№ҙеўЁжёҠжүҖиө пјүйҖ’з»ҷд»–пјҡвҖңиҝҷзҺүдҪ©жңүйқ’еҙ–зҒөж°”пјҢжҲ–и®ёиғҪеҠ©дҪ гҖӮе…Ҳз”ҹпјҢжҲ‘дҝЎдҪ гҖӮвҖқ
иҖҒеј д№ҹжҠұжӢійҒ“пјҡвҖңе°ҶеҶӣгҖҒе…Ҳз”ҹпјҢжҲ‘иҝҷе°ұеҺ»иҒ”з»ңеҪ“е№ҙзҡ„иҖҒејҹе…„пјҢиҷҪе·Іе№ҙиҝҲпјҢдҪҶжӢјдәҶиҝҷжҠҠиҖҒйӘЁеӨҙпјҢд№ҹз»қдёҚ让他们еҫ—йҖһпјҒвҖқ
еўЁжёҠжҺҘиҝҮзҺүдҪ©пјҢзңүй—ҙй№ҝеҚ°дёҺзҺүдҪ©е…үиҠ’е‘јеә”пјҢд»–зңӢеҗ‘йҳҝзҰҫпјҢзңјдёӯж»ЎжҳҜжё©жҹ”дёҺеқҡе®ҡпјҡвҖңдёүж—ҘеҗҺпјҢжҲ‘们е®ҲеҘҪиҝҷйӣҒй—Ёе…іпјҢеҶҚеӣһйқ’еҙ–еұұз…®иҢ¶гҖӮвҖқ
еӨңиүІжёҗж·ұпјҢйӣҒй—Ёе…ізҡ„йЈҺеёҰзқҖеҮ еҲҶеҜ’ж„ҸпјҢеҚҙеҗ№дёҚж•Јдәәеҝғзҡ„жҡ–ж„ҸгҖӮйҳҝзҰҫжңӣзқҖеўЁжёҠзҡ„иғҢеҪұпјҢзҹҘйҒ“иҝҷеӨӘе№ізӣӣдё–пјҢд»ҺдёҚжҳҜзҗҶжүҖеҪ“然вҖ”вҖ”жҖ»жңүдәәиҰҒз«ҷеҮәжқҘпјҢе®ҲзқҖеІҒжңҲйқҷеҘҪпјҢжҠӨзқҖдәәй—ҙе®үе®ҒгҖӮиҖҢиҝҷдёҖж¬ЎпјҢ他们дјҡ并иӮ©иҖҢз«ӢпјҢеҶҚжҠӨйӣҒй—Ёе‘Ёе…Ё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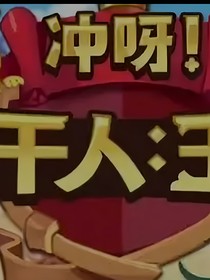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