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зңјеүҚдёҖй»‘зҡ„еҲ№йӮЈпјҢж„ҸиҜҶеҰӮеҗҢиў«зӢӮйЈҺеҚ·иө°зҡ„ж®ӢеҸ¶пјҢзһ¬й—ҙеқ е…ҘдәҶж— иҫ№зҡ„й»‘жҡ—гҖӮжғіжқҘиҜҘжҳҜзҒөеҠӣиҖ—з«ӯеҲ°дәҶжһҒиҮҙпјҢз»Ҹи„үйҮҢз©әиҚЎиҚЎзҡ„пјҢиҝһдёҖдёқеҠӣж°”йғҪжҸҗдёҚиө·жқҘпјӣеҸҲжҲ–жҳҜзҘ–еёҲзҲ·йҷ„иә«иҝҮд№…пјҢйӮЈиӮЎзЈ…зӨҙзҡ„зҘһйӯӮеҠӣйҮҸеғҸзғ§зәўзҡ„зғҷй“ҒпјҢеңЁжҲ‘иҝҷеүҜеӯұејұзҡ„иәҜеЈійҮҢзғҷдёӢдәҶйҡҫд»ҘжүҝеҸ—зҡ„еҚ°и®°вҖ”вҖ”жҖ»д№ӢеңЁеҪ»еә•еӨұеҺ»зҹҘи§үеүҚпјҢжө‘иә«дёҠдёӢзҡ„йӘЁеӨҙеғҸжҳҜиў«жӢҶејҖеҸҲиғЎд№ұжӢјжҺҘеңЁдёҖиө·пјҢжҜҸдёҖеҜёйғҪеңЁеҸ‘еҮәз»ҶзўҺзҡ„е‘»еҗҹпјҢй…ёз—ӣж„ҹйЎәзқҖйӘЁй«“еҫҖеӨ©зҒөзӣ–йҮҢй’»гҖӮ
ж··жІҢдёӯдёҚзҹҘиҝҮдәҶеӨҡд№…пјҢжҢҮе°–з»ҲдәҺи§ҰеҲ°дёҖдёқеҶ°еҮүзҡ„ең°йқўпјҢеёҰзқҖжіҘеңҹе’Ңи…җеҸ¶ж··еҗҲзҡ„жҪ®ж№ҝж°”жҒҜгҖӮжҲ‘иҙ№еҠӣең°жҺҖејҖжІүйҮҚзҡ„зңјзҡ®пјҢи§ҶзәҝжЁЎзіҠеҫ—еғҸи’ҷзқҖеұӮж°ҙйӣҫпјҢеҸӘзңӢеҲ°зҺ„йқ’жӢ–зқҖиҷҡжө®зҡ„и„ҡжӯҘжңқжҲ‘иө°жқҘпјҢд»–еҚҠиҫ№и„ёдҫқж—§иӮҝеҫ—иҖҒй«ҳпјҢеҺҹжң¬жЈұи§’еҲҶжҳҺзҡ„иҪ®е»“иў«зЎ¬з”ҹз”ҹж’‘жҲҗдәҶеңҶйј“йј“зҡ„жЁЎж ·пјҢеҳҙи§’иҝҳеҮқзқҖжңӘе№Ізҡ„иЎҖиҝ№пјҢеғҸжңөиў«жҸүзҡұзҡ„зәўжў…пјҢеҸҜйӮЈеҸҢзңјзқӣйҮҢзҡ„е…іеҲҮеҚҙжө“еҫ—еҢ–дёҚејҖпјҢеғҸжөёеңЁжё©ж°ҙйҮҢзҡ„жЈүзө®пјҢиҪ»иҪ»иЈ№зқҖжҲ‘зҡ„еҝғгҖӮиҖҢзҷҪзӢҗзӢёе·ІеҢ–еӣһдәәеҪўпјҢзҙ зҷҪзҡ„иЈҷж‘ҶеңЁеӨңиүІйҮҢжіӣзқҖжҹ”е’Ңзҡ„е…үпјҢеҘ№еҚҠи№ІеңЁжҲ‘иә«иҫ№пјҢе°Ҹеҝғзҝјзҝјең°е°ҶжҲ‘жҸҪиҝӣжҖҖйҮҢпјҢжҢҮе°–зҡ„жё©еәҰйҖҸиҝҮи–„и–„зҡ„иЎЈж–ҷжё—иҝӣжқҘпјҢеёҰзқҖиҚүжңЁзҡ„жё…йҰҷпјҢз«ҹеҘҮејӮең°й©ұж•ЈдәҶйӘЁзјқйҮҢзҡ„еҜ’ж„ҸпјҢеғҸеҲқжҳҘзҡ„第дёҖзј•йҳіе…үиҗҪеңЁеҶ°е°Ғзҡ„жІійқўдёҠгҖӮ
ж„ҸиҜҶеғҸжҳҜиў«еҚ·е…ҘжҖҘйҖҹж—ӢиҪ¬зҡ„жј©ж¶ЎпјҢеӨ©ж—Ӣең°иҪ¬й—ҙпјҢжҲ‘еқ е…ҘдәҶдёҖеңәжј«й•ҝеҲ°д»ҝдҪӣжІЎжңүе°ҪеӨҙзҡ„жўҰеўғгҖӮ
жўҰйҮҢзҡ„ејҖз«ҜпјҢжҳҜжҲ‘е°ҡеңЁиҘҒиӨ“дёӯзҡ„жЁЎж ·гҖӮйӮЈж—¶е®¶йҮҢе·Іжңүе“Ҙе“Ҙе§җе§җпјҢжҲ‘иҷҪжҳҜзҲ№еЁҳзӣјдәҶи®ёд№…зҡ„з”·еӯ©пјҢеҚҙжҒ°йҖўиҝһе№ҙзҒҫиҚ’пјҢең°йҮҢйў—зІ’ж— ж”¶пјҢиҝһж ‘зҡ®йғҪиў«еүҘеҫ—е№Іе№ІеҮҖеҮҖгҖӮзҲ№еЁҳжҠұзқҖжҲ‘е“ӯдәҶж•ҙж•ҙдёҖеӨңпјҢ第дәҢеӨ©жё…жҷЁпјҢ他们用дёҖ件жү“ж»ЎиЎҘдёҒзҡ„з ҙеёғе°ҶжҲ‘иЈ№зҙ§пјҢеңЁдёҖдёӘеҜ’йЈҺеҲәйӘЁзҡ„еҶ¬ж—ҘпјҢжҠҠжҲ‘дёўеңЁдәҶиҚ’йғҠзҡ„йӣӘең°йҮҢгҖӮеҢ—йЈҺеғҸеҲҖеӯҗдјјзҡ„еҲ®иҝҮи„ёйўҠпјҢйӣӘиҠұй’»иҝӣйўҶеҸЈпјҢеҶ»еҫ—жҲ‘зүҷе…іжү“йўӨпјҢе“ӯеЈ°з»Ҷејұеҫ—еғҸеҸӘеҝ«иў«еҶ»жӯ»зҡ„зҢ«гҖӮе°ұеңЁж„ҸиҜҶеҝ«иҰҒиў«еҶ»еғөж—¶пјҢдёҖеӣўжҜӣиҢёиҢёзҡ„жҡ–ж„ҸеҝҪ然еңЁиә«иҫ№и№ӯдәҶи№ӯпјҢиҪҜд№Һд№Һзҡ„е°ҫе·ҙжү«иҝҮжҲ‘зҡ„и„ёйўҠвҖ”вҖ”жҳҜеҸӘйҖҡдҪ“йӣӘзҷҪзҡ„е°ҸзӢҗзӢёпјҢе®ғжҠ–дәҶжҠ–иә«дёҠзҡ„йӣӘпјҢиң·еңЁжҲ‘иә«иҫ№пјҢз”Ёе°Ҹе°Ҹзҡ„иә«еӯҗзҙ§зҙ§иҙҙзқҖжҲ‘пјҢжҠҠд»…жңүзҡ„жё©еәҰйғҪжёЎз»ҷдәҶжҲ‘гҖӮеҗҺжқҘе®ғдёҚзҹҘе“ӘжқҘзҡ„еҠӣж°”пјҢз«ҹеҸјзқҖжҲ‘зҡ„иҘҒиӨ“пјҢдёҖжӯҘдёҖж»‘ең°з©ҝиҝҮжІЎиҶқзҡ„з§ҜйӣӘпјҢдёҖи·Ҝе°ҶжҲ‘жӢ–иҝӣдәҶдёҖдёӘйҒҝйЈҺзҡ„еұұжҙһгҖӮ
еҫҖеҗҺзҡ„ж—ҘеӯҗпјҢжҲ‘дҫҝдёҺиҝҷеҸӘе°ҸзӢҗзӢёзӣёдҫқдёәе‘ҪгҖӮе®ғжҜҸеӨ©еӨ©дёҚдә®е°ұеҮәеҺ»и§…йЈҹпјҢеёҰеӣһеҚҠеҸӘиЎҖж·Ӣж·Ӣзҡ„йҮҺе…”пјҢжҖ»дјҡе…ҲжҠҠжңҖе«©зҡ„йғЁеҲҶжҺЁеҲ°жҲ‘йқўеүҚпјӣжүҫеҲ°й…ёз”ңзҡ„йҮҺжһңпјҢд№ҹдјҡеҸјеӣһжқҘе ҶеңЁжҲ‘жүӢиҫ№пјҢиҮӘе·ұеҸӘе•ғйӮЈдәӣзҶҹйҖҸиҗҪең°зҡ„гҖӮе®ғеҡјз”ҹиӮүж—¶пјҢжҲ‘дҫҝи·ҹзқҖеӯҰпјҢиө·еҲқи…Ҙеҫ—зӣҙеҸҚиғғпјҢеҗҺжқҘд№ҹжёҗжёҗд№ жғҜдәҶпјӣе®ғе–қеұұ涧йҮҢзҡ„жіүж°ҙпјҢжҲ‘дҫҝи·ҹзқҖжҚ§иө·ж°ҙжқҘе–қгҖӮж—ҘеӯҗиҝҮеҫ—еғҸеұұжҙһеӨ–зҡ„зҹіеӨҙпјҢзІ—зіҷеҸҲеқҡзЎ¬пјҢеҚҙд№ҹзЈ•зЈ•з»Ҡз»Ҡең°жҙ»дәҶдёӢжқҘгҖӮзӣҙеҲ°жҹҗеӨ©пјҢжЈ®жһ—зӘҒеҸ‘еӨ§зҒ«пјҢеӨ©е№Ізү©зҮҘзҡ„ж ‘жһқиў«й—Әз”өеҠҲдёӯпјҢзғҲз„°еғҸз–ҜдәҶдјјзҡ„иҲ”иҲҗзқҖж ‘жңЁпјҢжө“зғҹж»ҡж»ҡпјҢе‘ӣеҫ—дәәзқҒдёҚејҖзңјпјҢиҝһз©әж°”йғҪзғ«еҫ—зҒјдәәгҖӮжҲ‘жӯ»жӯ»жҠұзқҖе°ҸзӢҗзӢёеҫҖзҒ«еңәеӨ–еӣҙеҶІпјҢиә«дёҠйӮЈд»¶з”Ёе…Ҫзҡ®зјқзҡ„з®ҖйҷӢе°Ҹиў„иў«йЈһжә…зҡ„зҒ«жҳҹзӮ№зҮғпјҢзҒ«иӢ—йЎәзқҖиЎЈж‘ҶеҫҖдёҠзӘңпјҢзҒјзғӯж„ҹйЎәзқҖзҡ®иӮӨ蔓延пјҢеғҸжңүж— ж•°ж №й’ҲеңЁжүҺпјҢеҸҜжҲ‘йЎҫдёҚдёҠз–јпјҢж»Ўи„‘еӯҗеҸӘжңүдёҖдёӘеҝөеӨҙпјҡвҖңеёҰзқҖе®ғйҖғеҮәеҺ»пјҢдёҖе®ҡиҰҒеёҰзқҖе®ғйҖғеҮәеҺ»гҖӮвҖқ
е°ұеңЁзҒ«иӢ—еҝ«иҰҒзҮҺеҲ°е°ҸзӢҗзӢёйӣӘзҷҪзҡ„зҡ®жҜӣж—¶пјҢе®ғеҝҪ然жө‘иә«жіӣиө·иҖҖзңјзҡ„зҷҪе…үпјҢеғҸиЈ№дәҶеұӮжңҲе…үдјјзҡ„гҖӮдёҖиӮЎжё…еҮүзҡ„еҠӣйҮҸзһ¬й—ҙд»Һе®ғиә«дёҠж¶ҢеҮәжқҘпјҢжөҮзҒӯдәҶжҲ‘иә«дёҠзҡ„зҒ«з„°пјҢеҗҢж—¶жңүиӮЎж— еҪўзҡ„жҺЁеҠӣжүҳзқҖжҲ‘зҡ„еҗҺиғҢпјҢи®©жҲ‘зҡ„и„ҡжӯҘеҝ«еҫ—еғҸйЈҺпјҢеҮ д№ҺжҳҜеңЁиҙҙзқҖең°йқўйЈһгҖӮеҸҜжІЎи·‘еҮәеӨҡиҝңпјҢдёҖзҫӨиә«зқҖйҒ“иўҚзҡ„дәәзӘҒ然еҮӯз©әеҮәзҺ°еңЁйқўеүҚпјҢдёәйҰ–зҡ„иҖҒиҖ…йЎ»еҸ‘зҡҶзҷҪпјҢзңјзҘһй”җеҲ©еҰӮй№°пјҢдёҚзӯүжҲ‘еҸҚеә”пјҢдҫҝжҠ¬жүӢжңқжҲ‘жӢҚжқҘдёҖжҺҢгҖӮеү§з—ӣеғҸжғҠйӣ·дјјзҡ„еңЁиғёеҸЈзӮёејҖпјҢжҲ‘ж„ҹи§үдә”и„Ҹе…ӯи…‘йғҪ移дәҶдҪҚпјҢе°ұеңЁж„ҸиҜҶжЁЎзіҠзҡ„зһ¬й—ҙпјҢжҲ‘еҗ¬и§Ғе°ҸзӢҗзӢёз”Ёжё…жҷ°зҡ„дәәеЈ°жҖҘе–ҠпјҡвҖңдҪ иө°пјҒеҲ«еӣһеӨҙпјҒжҲ‘д»ҘеҗҺдёҖе®ҡдјҡжүҫеҲ°дҪ пјҒвҖқ
еҶҚд№ӢеҗҺзҡ„и®°еҝҶдҫҝеғҸиў«жө“йӣҫйҒ®дҪҸдәҶпјҢеҸӘеү©дёӢж–ӯж–ӯз»ӯз»ӯзҡ„зўҺзүҮгҖӮ
жўҰеўғзҢӣең°дёҖиҪ¬пјҢжҲ‘е·ІжҳҜзҷҪеҸ‘иӢҚиӢҚзҡ„иҖҒиҖ…пјҢеқҗеңЁдёҖй—ҙз®ҖйҷӢзҡ„з«№еұӢйҮҢпјҢзӘ—еӨ–жҳҜиҗҪж»ЎзҷҪйӣӘзҡ„еұұгҖӮеҪјж—¶жҲ‘зҡ„дҝ®дёәе·ІиҮіеү‘зҘһеўғдёӯжңҹпјҢеңЁж•ҙдёӘдё–й—ҙйғҪиғҪжҺ’иҝӣеүҚдә”пјҢиә«иҫ№ејҹеӯҗж— ж•°пјҢеҚҙе§Ӣз»Ҳеӯ‘然дёҖиә«гҖӮиҝҷдёҖиҫҲеӯҗпјҢжҲ‘иёҸйҒҚеҚғеұұдёҮж°ҙпјҢд»ҺеҚ—еҲ°еҢ—пјҢд»ҺдёңеҲ°иҘҝпјҢйҖўдәәдҫҝй—®жңүжІЎжңүи§ҒиҝҮдёҖеҸӘйҖҡдҪ“йӣӘзҷҪзҡ„зӢҗзӢёпјҢеҸҜе§Ӣз»ҲжІЎжңүеҘ№зҡ„ж¶ҲжҒҜгҖӮзӣҙеҲ°йҳ–зңјзҡ„еүҚдёҖеҲ»пјҢеәҠеӨҙзҡ„жІ№зҒҜеҝҪжҳҺеҝҪжҡ—пјҢзҒҜиҠҜзҲҶеҮәдёҖзӮ№зҒ«жҳҹпјҢжҲ‘зҹҘйҒ“пјҢиҮӘе·ұзҡ„еӨ§йҷҗе·ІиҮігҖӮ
ејҘз•ҷд№Ӣйҷ…пјҢжҲҝй—ЁвҖңеҗұе‘ҖвҖқдёҖеЈ°иў«жҺЁејҖпјҢдёҖдёӘзҷҪиЎЈиә«еҪұжӮ„ж— еЈ°жҒҜең°иө°иҝӣеұӢпјҢи№ІеңЁжҲ‘зҡ„еәҠеүҚгҖӮжҳҜеҘ№пјҢиҝҳжҳҜи®°еҝҶйҮҢйӮЈиҲ¬жЁЎж ·пјҢзңүзңјеҰӮз”»пјҢеҸӘжҳҜзңјзҘһйҮҢеӨҡдәҶдәӣжҲ‘зңӢдёҚжҮӮзҡ„жІ§жЎ‘гҖӮеҘ№зңӢзқҖжҲ‘зҡ„е°ёдҪ“пјҢжҢҮе°–иҪ»иҪ»жӢӮиҝҮжҲ‘зҡ„и„ёйўҠпјҢиҪ»еЈ°е‘ўе–ғпјҢиҜӯж°”йҮҢж»ЎжҳҜеҢ–дёҚејҖзҡ„жҖ…然пјҢеғҸжөёдәҶж°ҙзҡ„жЈүзө®пјҡвҖңиҝҷдёҖдё–пјҢжҳҜжҲ‘иҙҹдәҶдҪ гҖӮдёӢдёҖдё–пјҢжҲ‘дёҖе®ҡйҷӘеңЁдҪ иә«иҫ№пјҢеҶҚд№ҹдёҚеҲҶејҖгҖӮвҖқ
ж—¶е…үд»ҝдҪӣеңЁжўҰеўғйҮҢиў«ж— йҷҗжӢүй•ҝеҸҲйӘӨ然еҺӢзј©пјҢеғҸеҝ«иҝӣзҡ„з”»еҚ·пјҢеҶҚеҫҖеҗҺпјҢдҫҝжҳҜж— иҫ№ж— йҷ…зҡ„з©әзҷҪпјҢд»Җд№Ҳд№ҹи®°дёҚжё…дәҶгҖӮ
зҢӣең°зқҒејҖзңјпјҢй…’еә—жҲҝй—ҙйҮҢеҲәзӣ®зҡ„зҒҜе…үи®©жҲ‘дёӢж„ҸиҜҶзңҜдәҶзңҜзңјпјҢеҘҪдёҖдјҡе„ҝжүҚйҖӮеә”иҝҮжқҘгҖӮиә«дёӢжҳҜжҹ”иҪҜзҡ„еәҠй“әпјҢеёҰзқҖйҳіе…үжҷ’иҝҮзҡ„е‘ійҒ“пјҢйј»е°–иҗҰз»•зқҖй…’еә—зү№жңүзҡ„ж¶ҲжҜ’ж°ҙе‘іпјҢж··еҗҲзқҖж·Ўж·Ўзҡ„йҰҷи–°ж°”жҒҜгҖӮжҲ‘еҠЁдәҶеҠЁжүӢжҢҮпјҢжө‘иә«иҝҳжңүдәӣеҸ‘жІүпјҢеғҸзҒҢдәҶй“…дјјзҡ„пјҢеҚҙе·Іж— еӨ§зўҚпјҢйӘЁеӨҙзјқйҮҢзҡ„й…ёз—ӣд№ҹеҮҸиҪ»дәҶдёҚе°‘гҖӮиҪ¬еӨҙзңӢеҗ‘еӣӣе‘ЁпјҢжҲҝй—ҙйҮҢз©әиҚЎиҚЎзҡ„пјҢеҸӘжңүзҺ„йқ’йқ еңЁжІҷеҸ‘дёҠжү“зӣ№пјҢд»–и„ёдёҠзҡ„иӮҝж¶ҲдәҶдәӣпјҢеҚҙдҫқж—§еёҰзқҖйқ’зҙ«иүІзҡ„з—•иҝ№пјҢеғҸиў«дәәжҢүдәҶеҮ еқ—ж·Өйқ’зҡ„йўңж–ҷпјҢе‘јеҗёеқҮеҢҖпјҢжғіжқҘд№ҹжҳҜзҙҜжһҒдәҶгҖӮ
иҖҢйӮЈеҸӘзҷҪзӢҗзӢёпјҢйӮЈдёӘеңЁжўҰйҮҢдёҺжҲ‘зӣёдјҙеҚҠз”ҹгҖҒеҸҲеңЁжҲ‘дёҙз»ҲеүҚи®ёдёӢиҜәиЁҖзҡ„зҷҪзӢҗзӢёпјҢж—©е·ІдёҚи§ҒиёӘеҪұ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ҝғйӯ”еү‘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ҚҒе…«иӢұйӣ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јҖеұҖй“ёе°ұж— дёҠж №еҹәпјҢжҲ‘й—®йјҺд»ҷи·Ҝпј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Һе •д№қе№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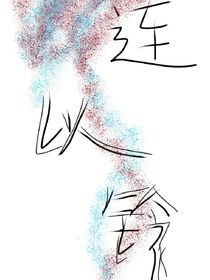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д»Ҙ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