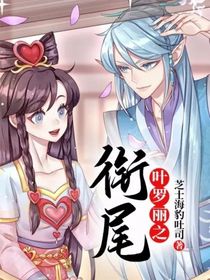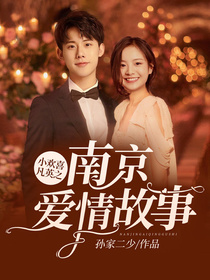第143章甄嬛传李卿卿143 会员加更 (3-1)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这里从兴京到吉林的地方几乎没有路,地势低洼积水,到处是黑色的土壤和飘落的枯叶,积雪不等旧雪化新雪又下了,渐渐地,这些地方积累成淤泥。深的地方有二三尺,浅的地方也有一尺多深。
两座山之间的积水形成了水泡子并不流淌。水色如铁锈一样,溅到身上就变成了红色。当地人称这种水叫红锈水。
山谷中,沉积下来的水成了水塘,积累的荒草凝聚成尘土,积累的尘土又生长出水草。新生的草浮在水面上,腐烂成泥的草沉入污泥中。
这些草的根系互相盘缠纠结,变成了一个个草墩子。马蹄踏在草墩子上边就陷不下去,踏偏了就陷进水中。所以,人只能下马步行,以避免摔落马下。当地人把这种草墩子叫塔头。
凡是有东北山区生活经历的人应该都知道吧(我也不是很确定),高士奇所说的这地方就是水草甸子,其实就是湿润的沼泽地。没有山区生活经历的人,可以看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录片时所过的“草地”,就知道怎么样了。
这个路其实真的也不好走。来回用了三个月,其实也算是挺快的速度了。
在这样的深山密林中,就算是修了皇帝御道,可是七万人的车马碾压,加之随行牲口的反复践踏后,这条路最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南怀仁在《鞑靼旅行记》中说得很实在,根据当时的情况去记录下来的,沿途任何城镇,也无法安顿这么大的人群住宿,更无法保证饮食供应。
而且前进的道路多是通过山岳丛林和山谷,所以一切一切的需用品,都必须随着这支队伍一同运输。
因而,无数的车辆、骆驼、骡、马,有的抄近道先走,有的就跟在东巡队伍的后面。那些运送帐篷、寝具,食具以及生活用品的车辆等等,随同这东巡旅行的巨大行列,根本无法分辨谁是谁,最后竟然都混成一个队伍了。
南怀仁还记载了,那些朝廷的显贵们怕牲口累,每天都要不断地换乘着他们的坐骑。皇帝用的,王爷们用的驮马,也都需要许多兵士牵着。
这些人和牲畜混合到一起疲疲踏踏地走着。“还有准备屠宰的牛群、羊群和猪群也一齐在两旁被驱赶著前进。”
在南怀仁看来,这条皇帝御道上,车轮声,马蹄声,牛哞马嘶猪嗷羊咩,加上人们的吆喝声,嘈杂而喧嚣。
现在想想,南怀仁说的那些早就为康熙东巡修筑好的光溜溜的平坦坦的“皇帝御道”,遭遇了这么多人,这么多牲口的践踏,会是什么样子呢?
绝对是在破坏草地。就跟现在破坏耕地,占地建路是违法的哦,没有国家政策允许是不能乱占用耕地的。
南怀仁说:“虽然这一切都和后妃们要经由的道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但是这车、人、兽相掺杂的不间断的大群,还是闹得尘埃云起。”
这还不够,南怀仁还偏要形容一下那种尘土飞扬中的感觉:“我们如同前进于无边际的云雾中,风从迎面或是倒面吹过来时,十五步到二十步远的地方,竟至什么也分辨不清。”
南怀仁大概害怕后人不了解这样的情形,补充了一些:“就是这般,这样的次序,我们约三个月间,几乎一日不停地向东方走了一千哩,并且用了同样的时间回来的。”
其实就是在赶路,赶路的人都是风尘仆仆的。累的很。
跟着康熙出巡吉林,竟然这么艰难,困苦累人。
综影视:娇软堪折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美少女战士:月亮粉碎
- 看情况更新封面图来源:小某书1816566363
- 0.6万字4个月前
- TF四代:感觉至上
- 开学缘更·多男主·养成系“拜托明明我最了解沈清诺了。”“什么嘛,姐姐最喜欢我了。”“想要我指导你也行,给我撒个娇我就答应你。”“如果某个姓沈......
- 6.1万字4个月前
- All婷:时空管理人
- 【这个是森林山与麓的小号】“执法者——BN8649尧慕婷,登录成功!”“我们所有人都不属于这……”“尧婷婷是你,我们亦是你……”“阿岁……回......
- 0.5万字4个月前
- 记录我看过的各种文
- 简介:记录和整理我看过的文,实在文荒的时候就可以找旧文来重温一下,也算是推文吧凭主观推文各种类型的文都有,可能每个平台都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完结......
- 127.2万字4个月前
- 叶罗丽之衔尾
- 时间线从浮云楼罗丽消失开始,当王默真的忘记身为叶罗丽战士时的一切,远离精英市学习,多年后与水清漓缔结契约回归精英市,再次回到仙境,重新遇见曾......
- 36.2万字4个月前
- 小欢喜凡英之南京爱情故事
- 已签约,禁转载岁月有你,此生足矣!你是我余生的小欢喜乔英子:方猴儿,你对别的女生温柔一点方一凡:英子,我的温柔只够对你一人前方预警,方一凡是......
- 131.8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