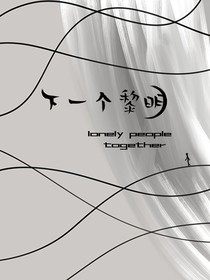第三十三章 (5-1)
“你还敢在这里反抗,说,为什么作业还没有写,你简直是家里的废物!以后只配去做打工的活儿。”那暴打声和辱骂声正从那孤独的房间里传出来,同时还弥漫着哭声。
是的,这栋位于山谷中一座相对破旧的公寓里,正传出一阵惊心动魄的家暴声。从窗外看向里边,一个大概四五十岁的中年父亲,正在无情地举起自己的酒瓶,砸向一个年纪不到二十岁的青少年。玻璃碎裂的声音混杂着少年压抑的闷哼,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像是一首扭曲而绝望的夜曲。
“少给我在这里哭,快点给我去写作业,不然我就要打死你!还有你,给我滚开!”他咆哮着,通红的眼睛像野兽般扫向门口那个瘦弱的身影——那是少年的母亲。她双手颤抖地捂着嘴,泪水早已浸透衣襟,却始终不敢上前一步。
她只是蜷缩在墙角,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任凭那粗鲁的声音一遍遍地撕裂着E小塔的脑子,也撕裂着她早已破碎的心。
E小塔紧紧地看着屏幕,只是满脸的奇怪,又说不出口来,因为他所看到的那个青少年--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嘴角渗着血,眼神却出奇地空洞。他没有再挣扎,也没有再哭喊。他只是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蜿蜒的裂缝,仿佛那里藏着某种答案。
他万万都没想到,眼前的这个男人,竟然就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面对亲人,甚至比那个曾经不停折磨他的Exe还更加无法解释的残忍。不过,他看到了父亲的旁边,正放着不少的酒瓶。他懂得,当纳克鲁斯喝酒喝醉后也会误伤到自己的兄弟上。可是…
为什么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呢?这对于E小塔来说,真是有些难以描述的奇怪。尤其这栋房子,让他突然想到不好的回忆之上。似乎,他脑壳里有一部分的基因已经觉醒了,E小塔正想要走过去拍塔尔斯。却发现,自己的脚像是被钉子扎住了样,几乎难以走动。
Tre塔尔斯始终保持着沉默,像一尊静立在阴影中的雕像。他站在房间最不起眼的角落,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呼吸的起伏,仿佛只是这间破败屋子里的一道幻影。可就在父亲又一次举起酒瓶、怒吼着要那个少年“滚去工地”的瞬间,Tre塔尔斯微微动了动下巴,朝着墙上的一处,极轻地努了努嘴。
那动作细微得几乎难以察觉,却像一道无声的指令,精准地落进了E小塔的眼中。
E小塔顺着那个方向望去——墙上,一幅被钉在木板上的画还挂着。那是一幅用廉价水彩和铅笔勾勒的画,纸张已经泛黄卷边,边角甚至被潮湿的墙壁浸染出斑驳的霉点。可画中的内容却鲜活得刺眼:一只灰色的狐狸,有着两条蓬松的尾巴,正安静地坐在山谷的悬崖边缘,仰望着星空。它的双眼是两颗深邃的红点,像是夜空中燃烧的星辰,又像是无声落下的血泪。狐狸的耳朵微微下垂,嘴角却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仿佛在守护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父亲的目光扫过那幅画,瞳孔骤然收缩。他像是被什么刺痛了神经,脸色瞬间由红转青,猛地冲过去,一把将画从墙上撕下。纸张在空中发出刺耳的撕裂声,仿佛一声呜咽。他攥着那幅画,在手中狠狠揉成一团,又狠狠砸在那个少年的脸上。
“你看看!你看看!”他咆哮着,唾沫星子喷在少年苍白的脸上,“你天天就只会画这些没用的东西!这些画能换米吗?能还债吗?能让你妈不被催租吗?滚出去搬砖,去洗盘子,去捡垃圾,都比你在这里做这种白日梦强一百倍!”
少年没有动,任由那团画砸在自己胸口,缓缓滑落。他的目光却死死盯着那被撕碎的画面——那只双尾狐狸,正从纸的裂缝中望着他,仿佛在说:“你还记得我吗?”
是的,那只狐狸,就是他自己。
灰色的皮毛,是他从小到大穿的那件旧毛衣;双尾,是他总想分裂出另一个自己,一个能逃离这里、能自由奔跑的自己;而那两颗红点般的眼睛,是他无数次在深夜里无声哭泣时,映在窗玻璃上的倒影。
在虚空中——e小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穿越末世后,觉醒顶级异能
- 0.7万字10个月前
- 傩
- 人有难,方有傩。傩舞起,百灾消。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交,秦宵在其中来回切换,什么都是假的,弟弟是假的,过往是假的,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是假的!......
- 3.3万字10个月前
- 星陨敦煌
- 2025年,敦煌莫高窟发现唐代密室,残卷记载玄奘法师带回的「星图金经」藏于西域某处,传说金经不仅藏有佛教至宝,更隐含古代天文与水利密码。境外......
- 3.5万字4个月前
- 等一个黎明
- 群像第一次写书无cp还请多多关照———世人皆知鬼神之说,也听过所谓的灵异事件但这其中还存在一个职业——摆渡人即是让亡灵找到归处,不成为孤山野......
- 1.2万字4个月前
- 怪谈缔造者
- 我叫林默,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缔造怪谈……
- 2.5万字2个月前
- 西游记10版宝可梦
- 系统的错误将青芸带到了宝可梦的世界,青芸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并带着宝可梦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却发现这里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年,接下来又会......
- 5.3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