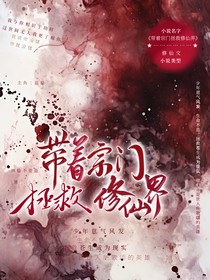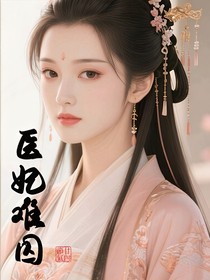豪强来欺生,胥吏阳奉违 (2-1)
县尉司的破败,并未出乎我的意料。那两名老衙役,一个姓赵,一个姓钱,都是在此地盘踞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条”,脸上堆着恭敬的笑,眼神里却透着打量和疏离。我简单问了几句县内治安概况,两人回答得滴水不漏,全是“尚可”、“偶有小贼”、“仰赖县尊大人洪福”之类的套话,实质内容一点也无。
我知道,初来乍到,想要立刻让这些地头蛇真心办事,绝无可能。当下也不点破,只让他们将积压的卷宗整理出来,便让他们退下了。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我并未急着翻阅卷宗,而是换上一身半旧的布衣,带着那名沉默寡言却手脚麻利的老仆,开始在丹徒县城内及周边村镇微服私访。这是我游学时就养成的习惯,官面上的文书固然要看,但真正的民情,往往藏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
几日走访下来,所见所闻,比钱县令的描述更为触目惊心。丹徒县的土地,确实多为贫瘠的江滩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百姓多以捕鱼、煮盐、或做些小手工勉强维生。而真正的症结,并非完全在于天灾,更在于**人祸**。
最大的“人祸”,来自两家本地豪强——掌控着沿江大半渔船和渔市的**张家**,以及把持着境内几处主要盐灶的**李家**。这两家与县衙内的胥吏,尤其是户房、刑房的几位书办、典吏勾结极深,盘剥百姓,几乎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渔民打的鱼,必须低价卖给张家指定的鱼行,否则便会被以“违反市易”为由刁难,甚至抢夺渔获;盐户煮出的盐,大半要无偿上缴给李家,美其名曰“盐课”,实则中饱私囊;普通农户更是苦不堪言,除了朝廷正税,还要承受各种名目的摊派和胥吏的敲诈勒索。
这日,我正在城西一处贫民聚居的陋巷中,听几位老人诉说李家盐霸如何欺压盐户,忽听得巷口传来一阵哭喊和叱骂声。
我循声走去,只见几个穿着家丁服饰的壮汉,正围着一户人家,一个为首的黑脸汉子,一脚踢翻了门口晾晒的鱼干,唾沫横飞地骂道:“老不死的!这个月的‘水例钱’还敢拖欠?真当张老爷的话是耳旁风吗?!”
被围在中间的是一位白发老妪和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老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张爷,行行好!上月江上风浪大,实在没打到几条鱼,连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有钱交例钱啊!再宽限几日,宽限几日吧!”
“宽限?”那黑脸家丁狞笑一声,“张老爷的规矩,概不赊欠!没钱?拿你这孙子抵债,去船上做苦力!” 说着就要去抓那少年。
少年吓得脸色惨白,死死躲在老妪身后。周围聚了些邻居,都是敢怒不敢言。
我眉头紧锁,怒火中烧。这“水例钱”分明是张家私自设立的苛捐杂税,竟敢如此公然强征,甚至要抓人抵债!
我正要上前,身边的老仆却轻轻拉了我一下,低声道:“老爷,初来乍到,不宜直接与张家冲突。那黑脸的叫张横,是张家的护院头子,手底下有些亡命之徒,与刑房的王典吏是拜把子兄弟。”
胥吏与豪强勾结!果然如此!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直接出手的冲动。硬碰硬,我现在势单力薄,未必能占到便宜,反而可能打草惊蛇,让自己陷入被动。
就在张横的手即将碰到那少年时,我分开人群,走了过去,脸上带着几分外地人特有的“好奇”与“不解”:
“几位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光天化日之下,怎的还要抓人?”
张横一愣,上下打量着我这身布衣,见眼生,语气蛮横:“你谁啊?少管闲事!张家收账,天经地义!”
词圣柳永:千古词宗系统助我逆天改命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带着宗门拯救修真界
- 苍生唯义,万世太平.“少年意气风发,生命不息,拯救苍生成为现实,他们亦是世人所歌颂的英雄”
- 0.7万字10个月前
- 我在仙门做执行
- 每逢佳节,别人“倍思亲”,我们“倍思勤”,有“活动”的地方,就有我们天宫域通途大道飞升路105号!!!
- 1.1万字10个月前
- 惧内皇帝和王爷的日常
- 骠骑大将军嫡女苏翊若,因父亲从龙有功,从小就和当时还是太子的夜姬尧玩在一起,他登基后风风光光的娶苏翊若进宫,立你为后,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
- 0.8万字8个月前
- 一不小心就养了个小疯子
- 神女x战神云千锦被自家母上大人一脚踢下了诛仙台说是要给那劳神子的战神渡劫云千锦:没错,我是免费劳动力10年后她假死回到神界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
- 0.9万字4个月前
- 医妃难囚改篇文
- 现代女医生苏瑶,在一次意外中穿越到古代,成为不受宠的王妃,卷入王府和宫廷的复杂纷争,初到古代的她,凭借现代医学知识,在王府中崭露头角,先是救......
- 1.5万字4个月前
- 鬼主的贡品非替身小娇妻
- 鬼主温客行因自己心爱之人被晋王杀害,疼恨于此,要晋王每一段曰子就要贡献一位身边至亲之人,可温客行却不知道……
- 5.0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