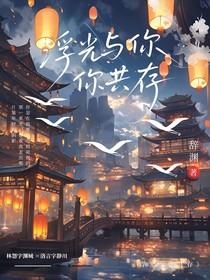第5章 生计陷困顿,虫娘伸援手 (2-1)
李文才那灼热的眼神和“五两银子”的报价,像一道闪电劈亮了我混沌的钱途。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词作本身可以卖钱,但“柳七真迹”这个IP,同样具有稀缺价值!在这个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首名人的亲笔手稿,对于粉丝(尤其是李文才这种有点钱又附庸风雅的文人)来说,简直就是绝版收藏品!
不过,我不能表现得太过急切。物以稀为贵,得保持逼格。
我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为难,沉吟道:“李兄厚爱,柳某心领。只是这信手涂鸦之作,恐污了贤弟法眼……”
“柳兄过谦了!”李文才急忙道,生怕我反悔,“兄之词章,已是绝妙。这墨宝更是……更是别具一格,颇有……魏晋风骨!”他努力寻找着褒义词来形容我那手歪歪扭扭的字。
我差点没绷住笑出来。魏晋风骨?这马屁拍得也太硬了。不过,我喜欢!
“既然李兄如此抬爱……”我故作矜持地叹了口气,“也罢,知音难觅。这首《鹤冲天》的手稿,便赠与李兄了。谈钱,未免俗气了。”
以退为进!先白送,建立高尚的文人形象,放长线钓大鱼。今天送他一份手稿,明天就可能通过他认识更多愿意花钱买“真迹”的“雅士”。
果然,李文才闻言,更是感动得不行,连连拱手:“柳兄高义!是小弟俗套了!日后柳兄但有新作,定要让小弟先睹为快!小弟在太学尚有几位同窗,对柳兄亦是仰慕已久,改日定当引荐!”
看,鱼饵这不就放下去了?还附带人脉拓展功能。
又客套了几句,李文才如获至宝地捧着那张写着“蚯蚓文”的破纸(在我眼里)走了。我掂量着怀里实实在在的三十两银子,心情大好。看来,在北宋实现“知识变现”和“IP运营”,大有可为!
接下来几天,我暂时在醉杏楼附近租了间便宜的小客房,算是有了个落脚点。白天,我一边用【基础书法体验卡】疯狂练习毛笔字(总不能一直靠“魏晋风骨”忽悠人),一边继续我的“定制词作”生意。
凭借着《鹤冲天》和《蝶恋花》(上阕)打出的名气,加上张嬷嬷不遗余力地宣传(她恨不得告诉全汴京的同行,她这里绑定了柳七的独家词源),陆续又有几家青楼派人来接触,或是邀请我去看看他们的姑娘,或是直接出价求词。
生意是有了,但我很快发现了问题。
首先,需求多样化,创作压力大。有的姑娘要艳词,有的要哀怨的,还有鸨母点名要能吸引豪客的“大气磅礴”之作。我这“借鉴”库虽然丰富,但也得对症下药,不能胡乱塞一首过去,不然砸招牌。
其次,沟通成本高。我得频繁出入各家青楼,跟不同的鸨母、姑娘打交道,察言观色,了解需求。这活儿不仅费脑子,还特么费腿!汴京城那么大,全靠11路公交车,几天下来,我感觉刚加的那点健康值又快耗尽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版权问题。这年头可没什么著作权法。我写的词,一旦给了一家,很难防止别家偷偷学了去传唱。虽然我强调“定制”,但模仿总是防不住的。长期下去,稀缺性就会打折扣。
得建立更稳定的合作模式和更高的壁垒。我一边嚼着索然无味的晚饭(外面的吃食又贵又一般),一边琢磨。
这天晚上,我正对着一首新“定制”的、需要描写边塞风光的词发愁(原主记忆里对西北的印象模糊,我也没去过,全靠想象,有点虚),房门被轻轻敲响了。
这么晚了,会是谁?难道是催租的?我警惕地站起身。
打开门,门外站着的,竟是醉杏楼的虫娘。她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裙,手里提着一个食盒,夜色中显得有几分单薄。
“虫娘姑娘?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惊讶。
虫娘脸上微红,低声道:“听闻公子近日为词作劳神,常常错过饭食。嬷嬷……嬷嬷让我给公子送些夜宵来。”她将食盒递过来。
词圣柳永:千古词宗系统助我逆天改命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江湖剑起
- 《剑舞江湖》以少年李剑风的江湖之旅为线索,展现了一个充满侠义与梦想的古代武侠世界。故事开篇便以一场路见不平的打斗,引出主角的侠义之心与对剑术......
- 3.3万字10个月前
- 浮生若梦篇:快穿!殿下,我要逃了
- 【虐文】【高冷男主与可爱女主的cp】这部小说以一个现代女孩穿越虚拟王国开始攻略男主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他们的爱恨纠葛,对于命运的无奈以及相互......
- 3.2万字8个月前
- 穿越后我成了江湖大佬
- 王玉穿越后成为了江湖出名剑客刘明和神医王之哲的徒弟16岁外出闯荡江湖认识了有钱有颜武功高强但身份神秘的沈北、长相妩媚但其实是个单纯的刚出江湖......
- 0.6万字4个月前
- 玉碎龙渊:燕王策
- 燕王府,牡丹盛放,酒香弥漫。以诗酒风流、醉卧花荫闻名的闲王江久恙,看似不问朝堂,只贪享富贵逍遥。然而,一次寻常的东宫探视、一场暗藏机锋的宫苑......
- 4.5万字4个月前
- 浮光与你共存
- 0.1万字4个月前
- 锁煜
- 先帝骤崩,遗诏破空而出,将缠绵病榻、性子犟得像块顽石的李煜推上九五之尊。龙椅未坐热,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镇国将军陆予谦便踏入宫闱。这位出身武......
- 3.6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