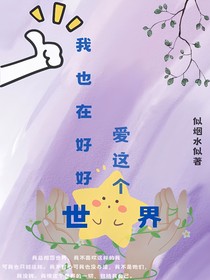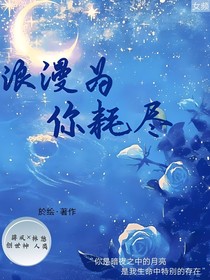第十三章 乡愁 (2-1)
盘锦的寒风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厂区里弥漫着塑料加热后的特有气味。但这一次,陈末看着车间里那些裹着厚棉袄、眼神里带着东北人特有韧劲和直率的工友,心里压着的石头似乎轻了些。尤其是当他认出其中一个沉默寡言、埋头调试注塑机的中年汉子,竟是他高中时隔壁班的体育委员张建军时,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暖意悄然滋生。
张建军也认出了他,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又惊喜的笑容,用力拍着陈末的胳膊:“哎呀妈呀!陈末?真是你啊!咋跑这疙来了?”得知陈末是新来的负责人,老同学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复杂,是期待,也是担忧。
“末儿啊,这厂子……唉,不好整啊。”下班后,张建军拉着陈末在厂门口的小馆子喝酒,几杯白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设备老掉牙,出的活儿比人家南方厂子成本高一大截,订单越来越少,大伙儿都提着心吊着胆,就怕哪天彻底黄摊子了。”
陈末默默听着,酒杯攥在手里。他想起海口,想起被裁掉的丰年农业,他不能再眼睁睁看着这群朴实的老乡,尤其是眼前这个老同学失业。
“建军,信我不?”陈末抬头,看着老同学的眼睛。
张建军一愣,随即重重点头:“那必须信!你说咋整,咱就咋整!这帮老伙计,都听我的!”
陈末心里有了底。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单打独斗。他让张建军成了他在车间里的“眼睛”和“耳朵”,哪个老师傅技术好肯钻研,哪个小组长有威信,哪台设备还有潜力可挖,通过张建军,他快速掌握了厂里真实的人员情况。
同时,他与海口的林薇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盘锦塑料厂主要生产日用品和简单的工业配件,技术含量不高,但成本是死穴。
“薇总,盘锦这边有一批积压的农用塑料筐,质量还行,你看海南那边果蔬基地有没有可能消化?” “林薇,帮我找几家南方性价比高的改性塑料原料供应商,要快,用量大。” “老赵,物流路线优化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边的货和海南那边的需求拼车,降低单件运输成本。”
他将海口的市场灵敏度、供应链资源和盘锦的生产基础艰难地嫁接起来。过程缓慢而痛苦,旧的生产习惯、僵化的流程阻力巨大,但好在张建军带着一帮信服他的老工友,全力配合陈末的每一项调整,哪怕只是微小的改进。
陈末不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更像一个嫁接资源的桥梁和一个激发内部活力的催化剂。他带着技术员蹲在车间改造老旧设备,降低能耗;说服老师傅尝试新的原料配方,虽然一次次失败;跟着销售跑周边县市,拉回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订单,稳住基本盘。
亏损的势头,就在这一点点的抠、一点点的磨、一点点的嫁接中,竟然真的被勉强止住了。报表上的数字虽然依旧难看,但那条下滑的曲线,似乎隐约有走平的迹象。
厂子里麻木的气氛开始消融,工人们看到这个年轻的领导不是来走过场等关门的,是真带着他们想办法找活路,虽然辛苦,但心里有了点奔头。
集团总部那边,刘伟听到盘锦厂居然还没死透,只是冷哼一声,并未过多在意。在他眼里,那不过是濒死前的回光返照,一个注定被抛弃的包袱,暂时还没排上裁撤日程表而已,不值得他再费心神。
陈末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里面忙碌的景象和呵出的白气,听着张建军用大嗓门指挥着搬运,心里稍稍松了口气。这只是暂时的稳住,远未到真正脱困的时候。
破径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也在好好爱这个世界
- 我也在好好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能不能也多爱我一点。我要的不多,父母健康长寿,兄弟姐妹健康平安孝顺。如果可以,请给我一点点私心,我想要一个独属......
- 1.1万字11个月前
- 浪漫为你耗尽
- 双男主/原创
- 0.7万字10个月前
- 校园里分分合合的故事
- 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改编的
- 0.5万字9个月前
- 得不到的一直在念想
- 反差的夏语和元初的故事
- 0.1万字8个月前
- 萌宝来袭,妈咪可以当咸鱼
- 报告,爸妈,在垃圾桶捡到了赚钱的萌宝,(还是女主亲生,女主咋不知道)原来是五年前的风流债留下来的,不过萌宝说他们很有钱会养我,女主在想是不是......
- 2.0万字8个月前
- 你选择谁
- 我抱白月光的大腿。
- 0.3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