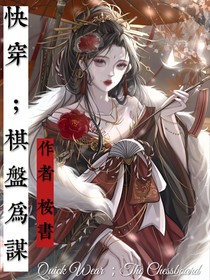第八章 松间石盒 (2-1)
暴雨连下了两日,直到第三日清晨才歇。天边挂着道淡淡的虹,书院后山的泥土里沁出草木的腥气。
沈砚秋揣着颗忐忑的心,避开往来的学子,悄悄往后山走去。谢临洲留下的字条像根刺,扎得他坐立难安——“未必是朝廷的人”,这话背后藏着的凶险,让他脊背发凉。
后山的路被雨水冲得泥泞,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心里反复默念着“第三棵松树”。白鹭书院的后山多竹少松,只有靠近山崖的地方长着几棵老松,想必就是那里了。
果然,走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就看见崖边挺立着几棵苍劲的松树。第三棵最为粗壮,树干需两人合抱,树根盘虬卧龙般扎进石缝里。
沈砚秋左右看了看,确认没人,才走到松树底下。他蹲下身,仔细打量着周围的石块,很快就发现了一块与周遭格格不入的青石板——比别的石头更平整,边缘还有撬动过的痕迹。
他深吸一口气,伸手去搬那块石板。石板比想象中沉,他用了些力气才将其挪开,露出底下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洞口不大,刚好能塞进一个巴掌大的木盒。沈砚秋伸手进去摸索,指尖果然触到了坚硬的木头。他将木盒取出来,见其表面刷着桐油,防水防潮,显然是早就备好的。
盒上挂着把小铜锁,锁孔里积着点灰尘,像是放了有些时日。沈砚秋翻来覆去地看,没找到钥匙,正发愁时,忽然想起谢临洲留在他那里的端砚。
他心头一动,转身往回走。回到舍院时,同屋的学子都去上课了,屋里空无一人。他快步走到桌前,拿起那方端砚,翻到背面——底部除了那个“谢”字,角落处还有个极小的凹槽,形状竟与铜锁的钥匙孔有些相似。
他试着将端砚底部往铜锁上凑,凹槽果然与锁孔严丝合缝。轻轻一转,“咔哒”一声,铜锁开了。
沈砚秋的心跳得飞快,打开木盒,里面只放着一卷油纸包着的东西。他展开油纸,发现是几张泛黄的纸,上面用朱砂画着些奇怪的符号,像是某种地图,又像是密信的暗号。
最底下压着一张字条,还是谢临洲的字迹,却比之前的潦草多了,像是写得很急:
“此乃父亲暗中调查的账目,涉及边关粮草与朝中官员勾连。若我一月未归,或京中传来不测,将此物交予吏部尚书周大人——切记,只能当面交,勿信他人。”
沈砚秋捏着那张字条,指尖冰凉。边关粮草?勾连官员?这与镇国将军遇袭、与父亲当年弹劾的贪腐案,会不会本就是一串连环?
他忽然想起谢临洲说过的话——“我爹说,当年的事,他没帮上忙,一直很愧疚”。难道镇国将军这些年,一直在暗中调查与沈父旧案相关的线索?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脚步声,赵姓学子哼着小曲走了进来。沈砚秋慌忙将地图和字条折好,塞进木盒,藏进自己的书箱底层,再用几件旧衣服盖住。
“沈砚秋,你没去上课啊?”赵姓学子见他脸色发白,有些奇怪,“刚才府衙的人又来问你了,问你谢公子走之前,有没有给你留过什么东西。”
沈砚秋的心猛地一跳:“你怎么说的?”
“我能怎么说?”赵姓学子撇撇嘴,“就说你俩也不熟,谢公子走得急,啥也没留。不过话说回来,你跟谢公子到底啥关系啊?怎么总有人来问你?”
沈砚秋没回答,只是望着窗外。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却照不进他心里那片陡然收紧的角落。
府衙的人已经开始查谢临洲留下的东西了。他们到底是谁的人?是冲着这份账本来的吗?
他摸了摸书箱的锁扣,那里面藏着的,不仅是谢临洲的信任,或许还有能掀翻朝堂的秘密,和两条人命的真相。
而他,一个无权无势的书院学子,突然成了这秘密的守护者。
月光藏心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后迟小姐赢麻了
- 迟洛桑从地狱里爬回来向曾经欺辱过她的人复仇。这一世,她定要好好活出自己的精彩,再也不被儿女情长耽误。我不会耽误你的,你看一眼我好不好。小侯爷......
- 3.2万字9个月前
- 快穿:棋盘为谋
- [架空-轻微蛇蝎美人-轻微宫斗宅斗-不无脑-不后宫/无记忆+无系统+不老套路+不狗血]单名:程、姝、月单名:谣、妩、姻感谢大家观看。这本书不......
- 8.3万字9个月前
- 大人!你家汤圆露馅了
- 萧锦瑜,世家公子,本可以享受平凡快乐的生活.不幸的是,他的损友南城雪带他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在艰难探索的道路上偶遇
- 0.2万字9个月前
- 云澜传奇(又名:江湖茶香)
- 天茗瓷影玉骨茶香在繁华且神秘的云澜大陆,有一个名为灵州的地方。灵州之中,天茗城宛如一颗璀璨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辉。天茗城以瓷器和茶叶闻名于世......
- 5.3万字7个月前
- 谁在笼中
- 4.1万字3个月前
- 古代皇帝图签
- 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历史上各个皇帝(不包括小政权不知名的皇帝)(除了新朝和魏晋南北朝)
- 1.8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