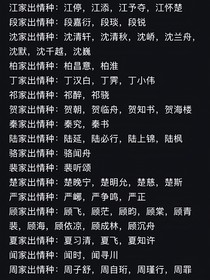第十二章 尽显才艺为助兴 (4-1)
庆功帐的羊毛毡子上还沾着未擦净的酒渍,陶釜里炖着的羯羊肉咕嘟冒泡,油星子溅在青铜炉沿上,滋啦一声化成白烟。冒顿刚放下啃得只剩骨茬的羊腿,指缝里还沾着血丝,突然抬眼扫过帐下,目光落在我身上时,喉结滚了滚,慢悠悠道:"那汉女胆大包天,竟敢在庆功宴上偷喝我的私藏马奶酒——罚她入主王帐,今夜与我共欢。"
最后五个字像块冰扔进滚油里,帐内瞬间静得能听见角落牧羊犬的呼噜声。
屠耆阏氏坐在左首第一席,头上插着三根雕花木簪,簪尾坠着的红玛瑙珠子本来随着她笑的幅度晃悠,这会儿猛地一顿,脸上的笑僵得像刚从冻河里捞出来的鱼。她穿的绛色绸裙绣着金线云纹,手往裙兜里一攥,帕子被绞成了麻花,指节白得发亮,偏还得扯着嘴角往下压,声音却抖得像秋风里的草:"单于...真会说笑,一个汉女罢了,哪配进王帐..."
她话音刚落,旁边几个小阏氏的眼都直了。挨着屠耆坐的那个叫阿古拉的,才十五岁,梳着双环髻,耳坠是银质的小铃铛,本来正用银匕挑着碟子里的奶豆腐,这会儿"哐当"把匕掉在盘子里,眼睛瞪得比碟子里的蜜饯还圆,扯着旁边人袖子小声喊:"入主王帐?大阏氏都没这待遇!她穿的那粗布裙都磨边了,凭啥啊?"另一个穿绿裙的阏氏更直接,撇着嘴往我这边瞥,嘴角撇得能挂油壶:"怕不是用了汉女那些狐媚手段,哄得单于晕头转向了!"
帐下的将领们更热闹。左屠耆是个络腮胡,脸膛黑得像烤焦的面饼,腰间悬着把镶宝石的弯刀,本来正跟人碰碗喝酒,闻言"咚"地把碗墩在案上,手按在刀柄上就想站起来,可刚抬屁股,又猛地想起前几天因为顶撞冒顿被斩的两个千夫长——那俩人头现在还挂在营门木杆上呢,他脖子一缩,又悻悻坐下,只是喉结咕噜噜转,眼神直往冒顿脸上瞟,那模样像极了想吠又不敢的狼狗。
右将朴氏缇是个瘦高个,眼窝深,鼻梁挺,脸上有道从眉骨划到下巴的疤,据说是跟月氏人打仗时留下的。他比左屠耆机灵,没敢动,只是端着酒碗嘿嘿笑,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人听见:"单于说罚就是罚,咱们跟着乐呵就是,管那么多干啥?再说...这汉女瞧着是比草原上的母羊还娇俏些。"
我站在帐中央,本来还捏着偷喝剩的半袋马奶酒,一听冒顿这话,手一抖,酒袋"啪"掉在地上。抬头看他时,他正斜倚在铺着黑狐皮的榻上,身上的玄色皮甲没卸,甲片上的铜钉在油灯下闪着光,嘴角却偷偷往上挑,黑眸里哪有半分凶戾?分明藏着点促狭,见我看他,还故意挑了挑眉,那模样,活像偷叼了鸡的狐狸。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哪是罚?分明是他怕我在帐下受欺负,故意当着全族的面给我立规矩:这汉女是我的人,你们都得掂量着。
冒顿拍了拍身侧的空位,那位置铺着张白狼皮,是他平时议事时才让亲信坐的。他没说话,只是抬了抬下巴,意思是让我过去。我却摇了摇头,快步走到榻边,挨着台阶坐下,还故意把脑袋往他大腿上一靠,声音压得低低的:"单于,我怕坐上去,帐下的刀片子要把我戳成筛子。"
冒顿低头看我,指尖在我发顶蹭了蹭,没说话,只是挥了挥手。侍女们早吓得站在帐角不敢动,这会儿见他摆手,赶紧端着新的马奶酒和烤羊排上来,陶釜里的肉重新咕嘟冒泡,帐里的气氛才算松了些,有人开始小声碰碗,只是眼神还总往我这边飘。
酒过三巡,屠耆阏氏突然"噌"地站起来,她大概是偷偷喝了口酒压惊,脸上泛着红,走到帐中央福了福身,声音软得像刚挤的羊奶:"单于得胜归来,我等姐妹无以为贺,愿献舞助兴,祝单于早日一统草原,踏平中原!"
饲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穿书后,在种田文里发疯
- 0.4万字11个月前
- 小樱好孕:宿主大大慢点生
- 快穿+美人+生子+多世界+异兽+部分双洁+无固定cp+小甜饼苏小樱出车祸后竟绑定生子系统,被告知为不同世界男主生子就能回现实且延寿增财!各世......
- 3.3万字10个月前
- 时空站之穿越完成中
- 这里是时空站,每位站长都是经过长期特训的。有什么想要完成的愿望或者遗愿吗?那么,夜晚12点就来樱花街找我们吧你想要的答案就在这里!
- 3.3万字10个月前
- 烛幕绝
- “我的心没了,难道你也没有吗”本文讲述的是:女主出身农村,父母重男轻女,被送到於无,意外被现实生活中的江烛穿越,前期凭着原女主意识与男主针锋......
- 0.3万字9个月前
- 玉锁千重门
- 田小薇,意外穿越到昭国京都典当铺小姐,方清歌。发现母亲古曼丽与丞相古毅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古家与皇室的复杂纠葛。从而渐渐与男主诸葛政渊产生微......
- 0.7万字8个月前
- 快穿:绿茶她专业拆cp
- 【已签约,禁止抄袭】没有人会不爱她,没有人能拒绝她,她是被神明偏爱的少女。无人可与之媲美的绝美容颜,超高的智商,无人能抵的魅力,她就是“完美......
- 9.3万字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