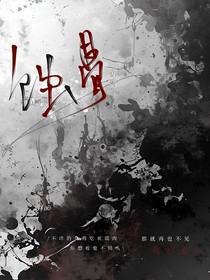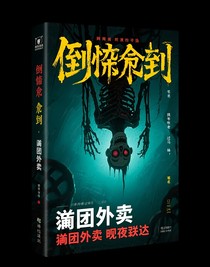第四章 地下室的回响 (4-1)
女人的歌声像一根浸了水的棉线,缠在林深的耳膜上,黏腻又阴冷。他攥着两个装着珊瑚珠的盒子,一路狂奔出槐安里巷口,直到撞在街角的路灯杆上,才踉跄着停下脚步。
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贴身的衬衫黏在皮肤上,冷得像冰。他低头看向怀里的木盒和证物袋——赵大爷刚塞过来的木盒上,缠枝莲的刻痕在路灯下泛着暗红色的光,而表姑那半串珠子的证物袋里,几颗珊瑚珠正微微发烫,像是有生命在里面搏动。
“别让珠子合在一起,千万别去地下室……”
赵大爷临终前的话在耳边炸开。可那歌声还在继续,咿咿呀呀的,唱的是一段早已失传的江南小调,调子婉转,却透着说不出的凄厉,分明就是从老宅的方向飘来的。林深猛地抬头望向槐安里深处,7号老宅的轮廓在夜色中像一头蛰伏的巨兽,窗口漆黑一片,只有那扇虚掩的木门,依旧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光。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不去。赵大爷死了,死状和表姑如出一辙——眼睛里淌出黑液,胸口插着白骨。而那根骨头上的“归”字,与老槐树上的“珠”字连起来,再加上铜镜上“它在找剩下的珠子”的字迹,像一张无形的网,正一步步把他拖向那个必须面对的地方。
地下室。
林深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自己停在巷口的旧摩托车。发动引擎时,轰鸣声惊飞了檐下的夜鸟,也暂时压过了那诡异的歌声。他没有立刻回老宅,而是骑车去了趟市档案馆——他需要知道更多关于沈家的事,关于那个失踪的沈小姐,关于这栋老宅的地下室。
档案馆的值班老头是个话痨,见林深半夜来查旧档案,起初还嘟囔着“年轻人不睡觉”,但在林深塞了两包烟后,便翻出了积着厚厚灰尘的“民国时期江城宅邸档案”。
“槐安里7号,沈家公馆……”老头戴着老花镜,手指在泛黄的纸页上划过,“民国三十五年建的,主人叫沈敬山,做丝绸生意的,当年可是江城的大户。他就一个女儿,叫沈清沅,听说长得极美,尤其爱穿月白色的旗袍,头上总戴着一串珊瑚珠,说是她母亲的遗物。”
林深的心猛地一跳:“沈清沅?那她后来……”
“失踪了。”老头翻到另一页,上面贴着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年轻女人站在老宅门口,穿一身月白旗袍,手里捏着一串红珊瑚珠,侧脸的轮廓与画中女人几乎重合,“民国三十七年夏天,说是跟人跑了,沈家派人找了三个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过半年,沈敬山就病死了,家道中落,房子几经转手,最后落到你表姑手里——哦,你表姑是沈敬山的远房侄女,当年沈家败落时,她还来打理过一阵子。”
“那地下室呢?档案里有没有提过老宅有地下室?”林深追问。
老头眯起眼睛,在档案里翻了半天,最后指着一张手绘的老宅平面图:“你看这里,主楼地基下面有个‘防潮地窖’,说是当年沈家存丝绸用的,后来沈敬山死后就封了。不过……”他突然压低声音,“我听我爷爷说过一嘴,当年沈家出事后,有人在半夜看到槐安里7号的后院冒过黑烟,还听到过女人的哭声,像是从地底下传出来的。”
林深的手指落在“防潮地窖”的标注上,那里用红墨水画了个小小的叉,旁边写着一行潦草的小字:“民国三十八年,封。”
民国三十八年,正是沈清沅失踪后的第二年。
离开档案馆时,天已经蒙蒙亮。林深买了把撬棍和一支强光手电,再次骑上摩托车驶向槐安里。巷子里静得可怕,只有他的脚步声和轮胎碾过积水的声音,赵大爷倒下的茶馆门口已经拉上了警戒线,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在勘察现场,闪光灯在晨雾中明明灭灭,像鬼火。
他绕到老宅后院,角门依旧虚掩着。这次,后院的荒草似乎比昨天更高了,齐腰的草叶上挂着晨露,在微光中闪着冷光,像是无数只眼睛在盯着他。老槐树上的刻痕“珠归”在晨光下看得更清,后面被磨平的地方,隐约能辨认出一个“原”字的轮廓。
珠归原……原什么?
槐安遗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四方极爱东篇(完结加番外
- 泰剧四方极爱泰剧原著小说
- 0.5万字9个月前
- 开局替身系统:我果然是真JOJO
- (JOJO同人+爽文+日常)论一个有着JOJO名字+★型胎记+替身能力的人究竟有多「HIGH」
- 1.3万字8个月前
- 蚀骨……
- 双男主be虐身也虐心叶雨很小的时候母亲出车祸离开了他,父亲一人把他拉扯到大,大学毕业后与楚明修同居,可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感情被消磨的一干二净,......
- 0.7万字7个月前
- 圣枪骑士的好朋友怎么会是吸血鬼?
- 从孤儿院初入社会的弗朗西斯竟然被女吸血鬼贵族看中并被转化为血族!但他最好的朋友杰克却是与吸血鬼有血海深仇的吸血鬼猎人!他们会决裂吗?还是联手......
- 2.4万字7个月前
- 倒悬尸契:冥团外卖今夜送达
- “零度城”的深夜,只有两种人还没睡:一种是等外卖的;另一种,是被外卖等的。试睡凶宅的沈槐,在4:44收到一份“冥团外卖”——送餐地址是他自己......
- 5.6万字3个月前
- 元浑探案
- 3.9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