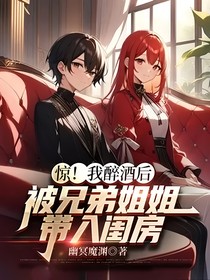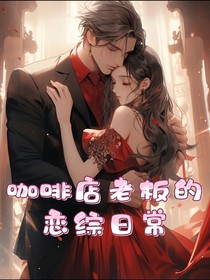第108章:渡口的船票 (2-1)
渡口的风带着水汽,吹得幡旗“哗啦啦”响。老艄公蹲在船头补网,竹篙斜插在岸边的泥里,木桨在水面晃出细碎的波纹。
你背着帆布包站在石阶上,手里捏着张泛黄的船票,边角被指甲磨得发毛。票面上的字迹模糊,只依稀能认出“往清河镇”三个字——那是你爷爷总念叨的地方,他说那里的石板路会“唱歌”,雨水打在上面能敲出《茉莉花》的调子。
“姑娘要搭船?”老艄公抬头,帽檐下的眼睛眯成条缝,“这船可是最后一班了,再等就得明天。”他指了指船尾堆着的麻袋,“刚收的新茶,赶在雨前送镇上,正好捎你一程。”
你踏上船板时,木板发出“吱呀”的呻吟,像在抱怨这突如其来的重量。船舱里弥漫着茶叶和潮湿木头的味道,角落里堆着几个竹篮,其中一个敞着口,露出半篮青绿色的梅子,酸气混着水汽往鼻尖钻。
“这梅子是前庄张婶给的,”老艄公解着缆绳,声音被风吹得散,“说让捎给镇上的女儿,姑娘要是渴了,尽管拿几个吃。”
船慢慢驶离岸边,你扶着船舷看两岸的芦苇荡。绿得发暗的芦苇秆子在风里摇,偶尔有白鹭扑棱棱飞起,翅膀扫过水面,惊起一圈圈涟漪。老艄公撑着篙,哼起段没头没尾的调子,调子像水面的波纹,荡着荡着就散了。
“您常走这条河?”你忍不住问。
“走了三十年喽,”他往船尾挪了挪,避开溅起的水花,“年轻时帮人运货,现在就送些茶啊果的,图个轻省。”他忽然指着左前方的浅滩,“看见那片歪脖子柳了吗?十年前有个教书先生,总在树下等船,手里总攥着本《论语》,见了谁都笑。”
你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柳树的枝条垂在水面,像谁散落的头发。“后来呢?”
“后来啊,”老艄公咂咂嘴,“娶了镇上绣坊的姑娘,就不常来了。前阵子见他挑着担子送绣品,鬓角都白了,倒还认得我,塞了块桂花糕,甜得齁人。”
船过石桥时,你看见桥洞下有个穿蓝布衫的妇人在浣衣,木槌捶打衣裳的声音“砰砰”响,惊飞了桥边的麻雀。她抬头看见船,扬手喊了句:“李伯,捎两斤新米不?家里刚碾的!”
老艄公笑着应:“下次吧,今儿船满着呢!”
你摸出怀里的旧照片,是爷爷年轻时在清河镇码头拍的,穿着粗布褂子,站在艘更大的木船旁,身后的幡旗上写着“顺安号”。照片边角卷了毛边,爷爷的脸有些模糊,但能看出嘴角扬着的笑。
“这码头以前可热闹了,”老艄公凑过来看了眼,“这‘顺安号’是镇上最大的船,后来沉在下游浅滩了,你爷爷当年就在这船上当伙计,专管收票。”他忽然指着你的帆布包,“包里是不是有个铜哨子?你爷爷以前总吹那个,说能镇住水里的‘怪东西’。”
你一愣,拉开包链,果然摸出个黄铜哨子,上面刻着细密的纹路。爷爷临终前塞给你的,说“到了清河镇,吹三声,就有人接你”。
“当年他吹这哨子,十里地外都能听见,”老艄公撑着篙,船慢慢拐进条窄水道,“有次运货遇着漩涡,全靠他吹哨子稳住了人心——那调子,跟我刚哼的可不是一回事。”
水面渐渐宽起来,远处能看见镇上的灰瓦屋顶。老艄公忽然停了篙,船借着惯性往前漂。“快到了,”他指了指码头边的石阶,“看见那个卖糖画的老头没?他认得你爷爷,你把哨子给他看,他就知道该带你去哪。”
你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石阶旁果然有个扎着草绳的糖画摊,老头正用铜勺在青石板上画着龙,糖丝在阳光下闪着琥珀色的光。
九个绝色未婚妻都在等着我离婚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惊!我醉酒后被兄弟姐姐带入闺房
- 16.8万字8个月前
- 猫猫赤苍的日常生活
- 这是一只喝牛奶就会醉的母猫和另外两只兽一起生活发生的故事
- 0.2万字8个月前
- 我能雕刻无限怪物!
- 【幕后】+【复活怪谈传说】+【无系统】+【无女主】饱受欺凌的少年,将无处宣泄的愤怒和恨意,都倾注在了他雕刻的怪物上。狼人,僵尸,吸血鬼,巨魔......
- 4.4万字7个月前
- 咖啡店老板的恋综日常
- 穿越正常的平行世界,男主表面上是个咖啡店老板,背地里是网上知名小说的作者。男主来到这个世界只想低调赚钱,没想到被前女友骗去参加一场恋综,在恋......
- 4.0万字7个月前
- 重生七零:被豪门找回后我带全家逆袭
- 1970年腊月深夜,北方农村王家破旧土坯房。屋内昏暗冰冷,土炕上铺着发霉稻草,墙角堆着红薯干。屋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形成内外对比。林晚因打......
- 15.8万字2个月前
- 沪圈太子爷(完结)
- 简介在上海武康路的梧桐深处,初入职场的设计师苏晚,与盛氏集团继承人、沪圈太子爷盛聿意外相撞,栀子花香与矜贵气场交织,开启一段奇妙缘分。招标会......
- 1.6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