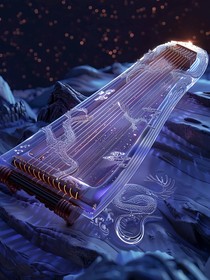他的想法 (2-1)
每天早晨九点,成真真都会把咖啡店的门推开一道缝, 挂上“正在营业”的木质牌子; 而Pierrot总在九点二十路过,假装被橱窗里的甜点吸引。
早晨八点十五分,城市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刚刚开始轰鸣。Pierrot攥着手中的海报宣传单,鞋尖踢着路牙石上滚落的一小块碎石,目光却钉死在街角那扇漆成墨绿色的门上。
到了九点
咔哒。
轻响在一片混沌的城市噪音里,清晰得几乎像幻觉。门被推开一道窄缝,先探出来的是半只系着黑色鞋带的白帆布鞋,接着,是成真真侧身挤出来的身影。晨光吝啬,只肯匀出一缕,恰好打亮她挽起袖口露出一截的手腕,和那块随着她踮脚动作轻轻晃动的木质牌子——“正在营业”。她总是要用点力,才能把牌子挂上那颗稍显倔强的钉子。
挂好了,成真真会退后半步,仰头看一下是否端正,然后转身消失在门后的暗影里。
而Pierrot的心脏在这五秒钟里,总是不讲道理地撞着胸腔。一下,两下,莽撞得像他第一次登台演出那样。
二十分钟后,九点二十整。Pierrot准时路过大敞的店门,鼻腔里提前灌满了那股浓郁到让人心安的被烘烤的豆子焦香。他的表演时间到了。橱窗里永远贴着咖啡的广告纸,Pierrot停下来,皱起眉,拿出研究出土文物的架势,仿佛那几张纸比刚出土的甲骨文文字还要深奥。
眼角的余光才是主菜。成真真在里面走动,擦拭蒸汽咖啡机,把玻璃柜里的蛋糕调整到最诱人的角度。偶尔有早起的客人推门,带响门楣上一串清脆的铜铃,她会说“早上好”,声音像给咖啡拉花时那抹最绵密的奶泡。
Pierrot计算过,从柜台到门口,是三步。从门口到我在的橱窗,是一米二。
一点二米。是Pierrot每天所能企及的全部奢望。是他和她之间,隔着奶油糖浆罐、收款机和无数杯外带拿铁的全部距离。
颜料的气味渗进指甲缝,洗不掉,像一种身份标识。Pierrot的世界是帐篷的红、小丑妆容的白、猛兽皮毛的虚假金黄。而她的世界,是咖啡豆的棕,是牛奶的纯白,是蒸汽氤氲里一切安稳又精致的日常。我们像两个不同齿轮,被毫无道理地抛进同一架机器里,徒劳地空转。
画笔蘸着深蓝的夜空色,Pierrot却调出了她眼睛的色泽。星星该用什么白?鬼使神差地,用了成真真挂牌子时,晨光落在她衣领上的那种白。画到后面,他停下了。
一个疯狂、卑微又孤注一掷的念头,像藤蔓一样勒住了Pierrot。
熬了整整一夜。在画布最不起眼的右下角,Pierrot用最细的笔,蘸着最亮的银漆,画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图案——一个被撕去一圈的咖啡杯套,那个她每天都会撕下来、折成小方块扔进小费盒的杯套。而在那“杯套”的中心,Pierrot写下了一个字母,小得如同星尘,几乎要融入卡牌的纹路里。
“P”———是他名字的开头大写字母。
这不是告白,这更像一个仪式,一次秘密的埋葬。Pierrot把所有无人接收的心动、所有清晨一点二米的凝望,全部封进这一点油彩里。
直到那天。天气糟得不像话,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雨要下不下。Pierrot照例完成他的橱窗观摩仪式,正准备离开,铜铃猛地一响。成真真竟然跑了出来,没打伞,怀里抱着厚厚一沓废弃的杯套——那是她折纸用的材料,她说过要攒起来做一件“艺术品”。
风毫无预兆地大作,像一只蛮横的手,瞬间将她怀里那叠五颜六色的纸环抢走,扬得到处都是。
pierrot与成真真同时愣了一秒,然后几乎同时弯腰去捡。风推着那些纸片跑,他们手忙脚乱地追,像两个在雨前试图拯救什么的笨拙的孩子。
终于,在一张被雨水打湿贴在路灯杆上的海报前,Pierrot摁住了最后几个顽固的杯套。雨点就在这时,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又大又沉。
怪诞马戏团(怪胎马戏团)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相亲对象不是人
- 乙女向小说,讲述了女主与妖魔鬼怪的爱恨情仇。
- 1.1万字9个月前
- 差一点小姐
- 0.5万字9个月前
- 灵魂摆渡之8号当铺冥王与阎王
- 故事中主人公冥王神茶阎王江辰江离兄弟故事由灵魂摆渡8号当铺冥王娶妻阎王双生兄弟蔓朱沙华双生姐妹忘川客栈三生姻缘十世轮回地狱少女死神少女孟婆十......
- 0.1万字8个月前
- 致命游戏:灵境逢生
- 「拆官配I原创女主」-一个分不清虚实的梦境,一场没有结果的游戏生死的交缠,命悬一线的生机她和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她彻底迷失了方向……-......
- 0.9万字8个月前
- 暗影之钥:午夜图书馆的窃贼
- 17岁的高中生林夏夕在生日当天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是一本封存百年的空白日记本和一枚刻着“时之眼”符号的青铜钥匙。当晚,她偶然发现钥匙能打开......
- 1.1万字7个月前
- 开局万亿冥币不一样的重生
- 咱们的主角再次重生,就是第二次重生了哦,但是这一次重生不止他一个人重生,咱们的小失也跟着回来了,就是咱们爱看陈失啊,就是不爱看这玩意儿的可以......
- 0.6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