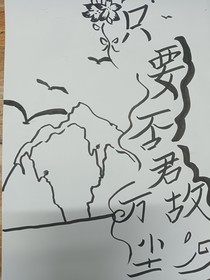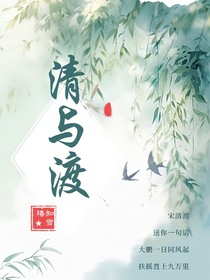第十一章:暗流涌动(二)
河西的炊烟重新升起时,沈砚却常在深夜登上城楼。月光洒在修复一新的城墙上,映出他鬓角新添的白发——那是阿史那夜离去后,河西的风霜刻下的印记。
“将军,朝廷送来的密信。”副将低声递上蜡丸,语气里带着凝重。
沈砚捏碎蜡丸,展开信纸的手微微一顿。信是长安旧部传来的,字里行间皆是暗流:安禄山已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私蓄战马五万匹,麾下蕃汉精兵十五万,近日更是以“御寇”为名,在范阳城北筑坛誓师,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呵,终于忍不住了。”沈砚将信纸凑到烛火上,看着火苗吞噬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传我令,让河西军即刻进入二级戒备,沿黄河一线增设烽火台,一旦发现朔方方向有异动,立刻报来。”
副将领命而去,城楼只剩沈砚一人。他想起三年前在长安,安禄山入宫觐见时,那双眼扫过朝臣的倨傲眼神。那时沈砚便觉此人必成大患,只是玄宗沉迷享乐,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只顾争权,无人肯听他的谏言。
如今河西虽稳,却孤立于西北。他派去联络陇右、安西诸军的使者尚未归来,而长安的消息越来越诡异:杨贵妃的兄长杨国忠与安禄山势同水火,朝堂之上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将军,西域商队带来了一批硫磺。”军需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还有于阗国送来的密报,说吐蕃赞普遣使去了范阳,似与安禄山有所勾结。”
沈砚眉头紧锁。吐蕃与安禄山勾结?这意味着一旦叛乱爆发,河西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境地——东面是安禄山的叛军,西面是虎视眈眈的吐蕃,南面还有蠢蠢欲动的党项部落。
他转身走下城楼,灯火通明的帅府内,河西地图摊在案上。沈砚拿起狼毫,在河西与朔方的交界处重重画了一道线:“必须打通与郭子仪的联系。”
郭子仪此时正任朔方节度使,驻守灵武,是朝中少数能与安禄山抗衡的将领。若能联合朔方军,便可在叛军西进时形成夹击之势。
三日后,沈砚挑选了十名擅长马术的死士,每人携带一封蜡丸密信,分五路前往灵武。临行前,他亲自为死士们斟酒:“此去路途艰险,若遇叛军盘查,可自毁密信。记住,你们的性命比信重要——河西需要你们活着回来。”
死士们饮尽酒,抱拳而去,马蹄声消失在黎明的薄雾中。
沈砚站在辕门外,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安禄山的叛乱一旦爆发,整个大唐都将陷入战火。而他守护的河西,将是帝国西陲最后的屏障。
“夜儿,”他轻声自语,仿佛阿史那夜就在身边,“你说,我们能守住这片土地,守住大唐的根基吗?”
风从河西走廊吹过,带着沙砾的气息,像是无声的回应。沈砚握紧腰间的佩剑,剑鞘上雕刻的狼图腾在晨光中若隐若现——那是阿史那夜送他的礼物,象征着草原与中原的共生。
他转身回府,案上的地图已被圈点得密密麻麻。无论前路多险,他都要走下去。为了河西的百姓,为了逝去的故人,更为了那个曾让他热血沸腾的大唐。
此时的长安,骊山华清宫的霓裳羽衣还在歌舞升平。无人知晓,一场席卷天下的风暴,已在西北的风沙中悄然酝酿。而河西的城楼之上,沈砚的目光早已穿透了千里烟尘,望向了东方即将燃起的烽火。
长安双璧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只要否君万故尘
- 一次意外让慕九霄重生至他与影十九的开始,即使知道了影十九有与他敌对的魔血,但是他还是愿意宠他的十九,这让影十九不敢相信。可是后来影十九失踪了......
- 0.1万字8个月前
- 清与渡
- 宋清渡,大宋嫡长公主,高傲,沉着,在她及笄的第二天,在外征战的鹤鸣风回来了,谁知后宫二皇子竟被人下了毒,鹤鸣风被安排去彻查此事,却拉上了宋清......
- 1.5万字8个月前
- 菜鸟结亲
- 身为暗卫、死于乱世的米景轩穿回百年前,我了被献至皇都的西域美人。谁知他大君:未来重整河山、成就千秋盛世的三皇子宋睿渊,如今竟是菜鸟一只。坐等......
- 0.4万字7个月前
- 向南走吧
- 无
- 0.6万字7个月前
- 宫斗穿书和系统大杀四方
- 带着系统穿越到古代宫斗直接大杀四方
- 0.3万字2个月前
- 九川赋
-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孩,在一座充满谎言和阴谋的宫殿里,凭借彼此的智慧和绝对的信任,抽丝剥茧,最终不仅揭露了惊天阴谋,实现了自我成长,更亲手摧......
- 2.7万字2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