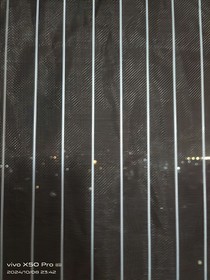“牛奶” (2-1)
火车停在荒原的第三夜,伊文洁琳发现女儿的睫毛结了霜。
起初她以为是月光——那层银白色的晶粒沿着孩子的睫毛生长,像初春河岸的芦苇芽。她呵着热气去暖,舌尖尝到铁锈味才意识到自己咬破了嘴唇。车厢里的哭嚎早已沉寂下去,只剩三十七具躯体在黑暗中交换体温。她解开棉袄纽扣,把六个月大的玛莎塞进贴胸的位置,肋骨被冰凉的襁褓硌得生疼。
"妈妈在呢。"她哼着丈夫教她的德涅斯特民谣,调子被冻得支离破碎。最后一次感受到女儿心跳时,她的拇指正抚过孩子发青的脚掌——那么小的脚,还不如她丈夫的烟盒大。那个总爱把烟叶分给战友的混账,被宪兵拖上卡车时还穿着睡裤。
黎明时分,玛莎变成了她怀里一块安静的油纸包。
马克拉克沃的雪地上,铁锹铲下去发出脆响。没有棺材,裹尸布是伊文洁琳的羊毛头巾,淡黄色,绣着向日葵图案。当冻土掩住那个小土坑时,她突然想起丈夫的烟盒还缝在自己大衣夹层里,锡皮上应该还留着体温。
后来她总在清晨第一个抵达奶牛场。
挤奶时金属桶沿结着冰碴,她就把玛莎的名字拆解成音节:М-а-ш-а,每念一个字母就挤压一次乳头。直到某天发现指关节裂开的血痕染红了牛奶,才惊觉自己已经忘记女儿眼睛的颜色。
现在她站在叶甫根尼的门槛上,两瓶牛奶在掌心摇晃。
玻璃瓶内壁凝结的水珠滑下来,像那列永远到不了站的火车窗上的泪痕。
伊文洁琳是从列宁格勒的雪里爬出来的。
她本是个农民的女儿,家里有黑麦田、桦树林,和一条总在春天泛滥的小河。革命前,她最大的烦恼不过是磨坊主克扣面粉,或者弟弟又偷吃了她的糖块。可战争来了,先是丈夫被征走,再是村庄烧成焦土,最后连糖和面粉都没了,只剩下配给卡上冰冷的数字。
于是她来到了马克拉克沃,成了集体农庄的会计。
说是会计,其实什么都干——清晨挤牛奶,中午核对账目,下午扛着斧头劈柴,晚上还要给夜校的工人们扫盲。她年轻,力气大,手指却意外地灵巧,能一边打算盘一边教女工们认字。人们都说,伊文洁琳的手是冻土上少有的、还能生火的东西。
“伊文洁琳,仓库的土豆发芽了!”
“伊文洁琳,奶牛场的秤坏了!”
“伊文洁琳,安德烈又逃学了!”
她总是应着,脚步匆匆地穿过雪地,围巾在风里翻飞,像一面褪色的红旗。
伊文洁琳不哭。
她埋掉女儿的那天,雪下得很大,坑挖得很浅,因为冻土太硬,铁锹只能啃出个勉强能放下孩子的凹陷。有人递给她一块木板,问要不要刻个名字。她摇摇头,说不用了,反正春天来了,雪一化,就什么都找不到了。
人们以为她会崩溃,会像其他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样,在夜里尖叫着醒来,或者抱着小小的衣服发呆。但伊文洁琳没有。
她只是干活。
清晨四点,奶牛场的灯还没亮,她已经蹲在牛棚里,手指熟练地挤压着温热的乳头。牛奶“滋啦滋啦”地喷进铁桶,白色的泡沫溅在她的围裙上。
同一个太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鬼相阴阳传
- 刚毕业即失业的女大学生——闫琳,遭闺蜜算计背负庞大业障,为活命无奈踏上阴阳之路,算命捉鬼积载功德。且看她如何抗命!
- 3.3万字6个月前
- 我和袁向阳的往昔
- 袁向阳是我2018年去新源县认识的好朋友,怀念起和他曾经的点点滴滴,那些熟悉的场景至今仿佛还历历在目。现在依旧和他还有微信联系,但是回不到以......
- 0.5万字6个月前
- 问海棠
- [无限流][无cp][友情最重要]主角温棠忧无限流文笔一般简介懒得写自己看主角你们认为是男是女都行自小温棠忧便知道一个事“父亲不爱自己…”“......
- 2.0万字5个月前
- 坡东——黎明将至
- 黎明星死在了黎明前,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只为那一瞬间的璀璨--我们都是罪人。(封面侵权会删的)
- 1.5万字2周前
- 进化成为无上神龙
- 重生类别最终进化无人能敌还有系统哦!
- 0.4万字昨天
- 欢迎来到女校,雨宫同学!
- 【著丨雨雾连城】【封面图源网络侵删】作为紫阳花女子学院高中招收的第三批男学生,同时也是本届唯一一个男学生,雨宫月见遇见了大问题。可爱外表与性......
- 0.7万字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