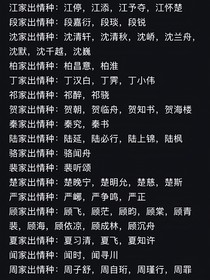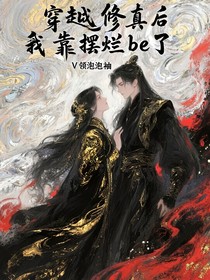婆媳的丝线 (2-1)
京城里有户姓周的人家,婆媳俩总吵架。婆婆说儿媳绣的花样“太张扬,不像个本分人”,儿媳说婆婆的绣法“太陈旧,跟不上时兴”,家里的气氛比腊月的冰窖还冷。
“周大嫂昨天又把绣绷摔了,”卖花的老婆婆跟枝枝念叨,“好好的一块云锦,被剪得稀碎,多可惜啊。”
枝枝正在学堂教孩子们用丝线画圆,闻言眼睛一亮:“我有办法了。”
她让人把周婆婆和周大嫂请到宫里的绣房,指着墙上挂着的凤凰风筝:“你们看这风筝上的金线,是淑妃娘娘和先帝一起绣的——娘娘爱用活泼的缠枝纹,先帝就用沉稳的回字纹配着,反而更出彩。”
周婆婆看着风筝上的纹路,嘴角动了动——她年轻时也爱绣缠枝纹,是被生活磨得渐渐忘了怎么弯出柔和的弧线。周大嫂则盯着那些回字纹,突然发现它们虽然规矩,却在转角处藏着细小的卷草,像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柔。
“今天我们绣幅‘双生花’吧。”枝枝拿出块素白的绸缎,在中间画了条线,“左边请婆婆绣,右边请大嫂绣,最后我们把它缝在一起。”
周婆婆选了沉稳的靛蓝色丝线,绣的是江南的老梅,枝干苍劲,花瓣却带着圆润的弧度;周大嫂挑了鲜亮的桃红色,绣的是西域的牡丹,花瓣张扬,花芯却用了婆婆擅长的盘金绣,像把锋芒藏进了温柔里。
绣到一半,周婆婆的手抖了抖,梅枝的线条歪了。周大嫂没说话,悄悄用桃红色丝线在歪处绣了朵小小的桃花,像给老梅添了个春天的注解。周婆婆看着那朵桃花,突然叹了口气,用靛蓝色丝线在牡丹的花茎上,绣了圈细细的回字纹,说“这样就稳当了”。
太阳落山时,“双生花”绣好了。老梅和牡丹在绸缎上依偎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却像早就该长在一起,连针脚都透着默契。枝枝把绣品裱起来,挂在绣房最显眼的地方,说“这是今年最好的绣品”。
周婆婆回家后,第一次拿起儿媳买的亮丝线,在给孙子做的肚兜上,绣了朵小小的牡丹;周大嫂则翻出婆婆压箱底的老绣样,在牡丹的边缘,加了圈回字纹的边。邻居们都说,周家的院子里,终于飘出了笑声,比丝线还甜。
后来,这对婆媳开了家绣坊,叫“双生记”。她们教城里的姑娘绣花,教她们“既要会绣老梅的风骨,也要懂牡丹的热烈”。绣坊的招牌,是枝枝用墨笔写的,笔画里既有周婆婆的沉稳,也有周大嫂的灵动,像两个终于和解的灵魂,在宣纸上开出了花。
秋收时,江南的粮官送来急报:新收的稻子有一半发了芽,百姓们急得直掉眼泪,说“这是天要饿死人啊”。
赵珩看着奏折,眉头紧锁。发芽的稻子不能做口粮,可扔了又太可惜,国库的存粮虽然充足,却也经不起这样的浪费。
“父皇,我想去江南看看。”枝枝正在学堂教孩子们用稻穗编小篮子,闻言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我祖母说过,发芽的种子,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江南的稻田里,果然一片愁云。老农们蹲在田埂上,看着堆成小山的发芽稻子,唉声叹气。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农,正把发芽的稻子往水里扔,说“不如喂鱼,还能换口肉吃”。
“老伯,别扔!”枝枝跑过去,捡起一把发芽的稻子,嫩绿的芽尖在她掌心颤动,像一群刚出生的小鸟,“这是最好的种子啊。”
老农直摇头:“公主不懂,这芽发得太乱,种下去也长不好庄稼。”
“我们可以让它换个地方长。”枝枝指着旁边的菜地,“把它种在菜窖里,不见光,就能长成豆芽,又脆又嫩,能当菜吃。”
她蹲在地上,用树枝画了个简易的菜窖:“底层铺沙子,洒上水,把发芽的稻子铺上去,再盖层湿布,保持湿润,不出十天,就能长出白白胖胖的豆芽。”
老农们半信半疑地试了。十天后,菜窖里果然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豆芽,白白嫩嫩,像一群挤在一起的圆。炒着吃,脆生生的;煮着吃,鲜津津的。百姓们都说:“原来发芽的稻子,不是灾,是福啊。”
霍总,您的小枝枝长歪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时空站之穿越完成中
- 这里是时空站,每位站长都是经过长期特训的。有什么想要完成的愿望或者遗愿吗?那么,夜晚12点就来樱花街找我们吧你想要的答案就在这里!
- 3.3万字10个月前
- 凹凸:我们只是个打工的
- 当四个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穿越凹凸会有怎样的火花。
- 3.3万字9个月前
- 穿越之我爱上了美女搭档
- 一朝穿越我成为了终极女主,结果改变剧情!摆脱男主,撩搭档,开小挂...是有着上帝视角的女人呵呵~男人?有我老婆好?
- 4.0万字8个月前
- 快穿:七个人的攻略
- 1.高岭之花温柔学长马嘉祺x(校园)2.粘人的小狐狸丁程鑫x3.奶狗变狼狗刘耀文x4.喜欢抱抱的兔兔贺峻霖x5.会下蛊的苗疆少年严浩翔x6.......
- 0.2万字4个月前
- 穿越修真后我靠摆烂be了
- 【穿越+马甲+修仙+逆袭+养成+腹黑反派】裴念,本是21世纪一个命苦医学生,因期末考来临半夜复习猝死,一朝穿越差点被天雷劈死,为了活命被迫绑......
- 2.1万字3个月前
- 快穿:恶毒女配她靠弹幕爆改权谋剧
- 【弹幕系统+快穿+宫斗爽文】十八线演员慕昭宁绑定弹幕系统,被迫穿成各类架空历史剧中的恶毒女配。眼看死局将至,眼前竟飘过全网吐槽剧透!利用信息......
- 1.5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