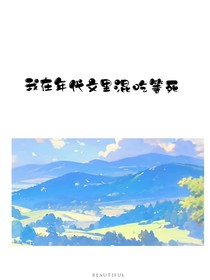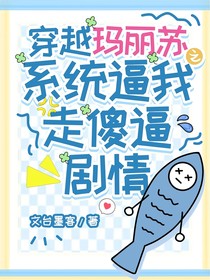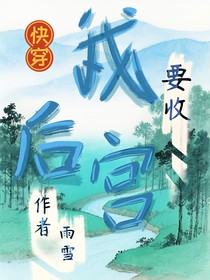会生长的…… (3-1)
入秋后,京城里爆发了小规模的瘟疫。起初只是几个乞丐上吐下泻,没过几天,连宫里的太监都开始发病,太医院的药材很快告急。
“是痢疾。”枝枝看着太医院的脉案,芯片里的医学数据库飞速运转,“需要马齿苋和金银花,这两种草药性凉,能杀菌止泻。”
太医们面面相觑:“公主有所不知,马齿苋是田埂上的野草,登不得大雅之堂,谁也没敢入药啊。”
枝枝没多说,带着学堂的孩子们去了郊外的田埂。她教孩子们辨认马齿苋:“看,叶子是椭圆的,茎是红的,掐断会有白色的汁——这是土地给我们的药。”
孩子们挎着竹篮,蹲在田里采药,笑声惊飞了田埂上的麻雀。小石头采得最认真,他说:“公主姐姐,这草是不是也像圆一样?看着普通,其实藏着大本事。”
枝枝笑着点头,指尖划过马齿苋的叶片。阳光透过叶片的脉络,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像无数个小小的太阳。
回到宫里,她把马齿苋和金银花按比例配好,亲自在药圃里熬煮。药香混着泥土的气息飘满宫廷,闻着竟不像普通药汤那样刺鼻。
“公主,这野草真的能治病?”负责煎药的老太监将信将疑,“万一吃出人命……”
“我先喝。”枝枝端起药碗,一饮而尽。药汁微苦,却带着草木的清香,像把田埂上的阳光喝进了肚子里。
三天后,喝了药的病人渐渐好转。赵珩看着枝枝熬药熬得发红的眼睛,突然让人把太医院的药圃改了半亩,专门种马齿苋、蒲公英这些“野草”。
“陛下,这不合规矩啊。”药圃的管事急得直跺脚,“药圃里种的都是人参、灵芝这些珍品……”
“规矩是人定的。”赵珩指着正在给野草浇水的枝枝,“能治病的,就是好药。就像能暖人的,就是好话,不管它是不是从草莽里来的。”
枝枝还教百姓用草木做日常的药。她让孩子们把薄荷晒干,缝进香囊里,说“这能提神醒脑”;让妇人把艾草编成草绳,说“这能驱虫避瘟”;让农夫把南瓜子炒熟,说“这能赶走肚子里的虫”。
有次匈奴使者来议和,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太医们束手无策。枝枝端去碗马齿苋汤,使者看着碗里的“野草”,脸色发青。
“这是我们这里的‘安心草’。”枝枝笑着说,自己先喝了一口,“喝了它,就不会再想家想得心焦了。”
使者半信半疑地喝完,当天就好了大半。他回去后,在给匈奴王的信里写道:“大靖的公主,能用野草治病,他们的心里,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更柔软。”
那年冬天,匈奴送来一车晒干的麻黄草,说“这是我们草原的‘驱寒草’,能治你们的风寒”。赵珩让人把麻黄草种在药圃的另一边,和马齿苋挨在一起,像两族的人,终于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的答案。
江南之行最终在第二年春天成行。枝枝没坐龙舟,而是和赵珩一起,穿着普通百姓的衣裳,骑着马走在江南的石板路上。
“父皇你看,这里的桃花真的会结果。”枝枝指着路边的桃林,枝头挂着青涩的小桃子,像无数个没长大的圆,“母妃说的没错,圆滚滚的果子,才是花的归宿。”
赵珩勒住马,看着她伸手去够桃子的样子,突然想起淑妃当年也是这样,总爱踮着脚摘树上的果子,说“你看这果子多圆,像不像我们以后的日子”。那时的他总笑着说“朕是皇帝,想要什么没有”,却没懂她要的不是果子,是那份摘果子的寻常欢喜。
他们在江南的集市上停了下来。枝枝看见个卖花的老婆婆,篮子里的桃花蔫蔫的,没人问津。她拿起支桃花,用随身携带的炭笔在纸上画了朵盛开的桃花,旁边写着“买支桃花,换个春天”。
“婆婆,把这个贴在篮子上吧。”枝枝把画递过去,“这样大家就知道,您的花能带来春天啦。”
老婆婆半信半疑地贴上画,没过一会儿,篮子里的桃花就被抢购一空。有个书生买了支花,笑着说:“姑娘的画比花还好看,不如我买您的画,花送您?”
霍总,您的小枝枝长歪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在年代文里混吃等死
- 姜珠一朝穿越,成了乡下极品的女儿,努力过上好日子,到后期逐渐觉醒记忆。穿越搞事业女主,福气女主,重生女配,个个大显神通。(女主有金手指+架空......
- 2.8万字10个月前
- 重生后成为家人的团宠
- 重生
- 0.6万字9个月前
- 龙傲天男主爆改万人迷
- 一个一心向道的逗比龙傲天男主被各界争抢的故事。
- 1.7万字8个月前
- 面包奇遇记
- 如果给你一块神奇的面包,吃了之后就可以逆转时空,你愿意吗?杨小橙有一家神奇的面包店,取名【云端的橙子】,在这里,只有有缘人可以吃到神奇的面包......
- 0.8万字8个月前
- 穿越玛丽苏之系统逼我走剧情
- 鹿小溪意外死亡穿进一本玛丽苏小说,系统承诺:“只要走完剧情,你就能复活。”可很快,她发现一切都不对劲——►男主傅薄言看她的眼神,让她感觉莫名......
- 3.3万字4个月前
- 快穿:我要收后宫
- 我想咋写就咋写,爱咋咋地,爽就完了(直接看第一章开头吧)
- 3.8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