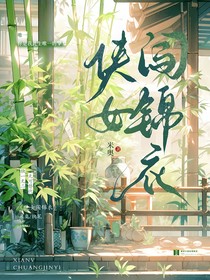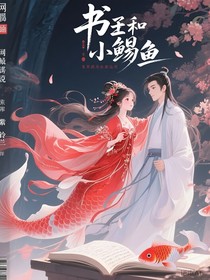摄政王的白月光:死了五年的他,竟藏在灾镇? (3-1)
眨眼数个春秋已过,檐角的铜铃蒙了层薄锈,风过之时,再难发出清脆的响,倒像是谁在低低地叹息。
院中的那株海棠树又高了些,枝桠探过墙头,将斑驳的光影投在青石板上,恍惚间还能看见当年盛瑜倚着树干笑的模样——那时他总爱折一枝半开的海棠,塞进许宛手里,说这花配得上他眼底的光。
可如今,花开花落又几番,掌心再无海棠香。
深秋的雨缠缠绵绵下了整月,阶前的青苔吸足了水汽,在砖缝里疯长,像极了那些蔓延在心底的思念,扯不断,理还乱。
许宛独坐院中,指尖抚过石桌上那只盛瑜用过的玉盏,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漫到心口,惊起一阵细密的疼。
他望着檐外连绵的雨幕,恍惚间又看见盛瑜身披银甲,立于城门之下,回眸时眉眼带笑,声音穿透风雨:“阿宛,等我回来,陪你看这万里河山真正安定。”可那笑容碎在了那年寒冬。
城破之日,火光染红了半边天,他的尸骨混在万千忠魂之中,连块完整的墓碑都没能留下。而许宛,终究是独自坐在了权力的顶峰。
“呵……”许宛低低地笑了一声,笑声里裹着化不开的苦涩,“人死不能复苏,死去的人已经不在了。”他抬手按了按发紧的眉心,指腹触到一片冰凉,不知何时已沁了泪。“但活着的人,仍然要活着。”他曾不止一次想随他而去,可每当闭上眼,总能听见盛瑜最后的嘶吼——“守好这国,护好这民!”
想死?呵,也死不了。
他不是为了这所谓的盛世平安。这盛世之下,藏着多少白骨,他比谁都清楚。他是为了盛瑜拼死守护的那片国土,为了他剑指之处、拼死也要护住的百姓,也是为了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幼子——那是他亲手挑选的“傀儡”,却也是他必须护周全的象征,是他与盛瑜未竟之志的延续。盛瑜的血洒在了那里,他便要替他看着,看那片土地上的人安居乐业,看炊烟袅袅,岁岁平安。
雨停时,天已破晓。许宛起身拂去衣上的凉意,铜镜里映出一张清瘦却坚毅的脸,眼底的红血丝未加掩饰,下颌线绷得紧直,那是常年居于上位的冷硬。他随手将散乱的衣襟系好,换上一身玄色蟒纹朝服,腰间玉带扣得一丝不苟,推门而出时,廊下侍立的内侍们齐刷刷跪了一地,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太极殿上,百官肃立。户部尚书颤巍巍地出列,花白的胡子抖得厉害,声音带着难掩的焦急:“摄政王殿下,宁兴郡下属的清河镇遭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堤坝溃决,良田尽毁,百姓流离失所,恐生民变啊!”
殿内一片寂静,连香炉里的烟都似凝固了。清河镇偏远贫瘠,洪灾过后必有瘟疫,谁都清楚这差事是块烫手山芋。更重要的是,如今朝政尽出摄政王之手,连五岁的小皇帝都得看他眼色,谁敢在这种时候触他霉头?
许宛站在龙椅之侧的蟠龙柱旁,比那金銮宝座更有压迫感。他眸光微沉,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玉带——清河镇,那是盛瑜的 一直想去却没去的地方 。
“本王,亲往清河镇赈灾。”他上前一步,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空旷的大殿里掷地有声。
满朝文武皆是一怔,不少人偷偷抬眼打量他。谁都知道摄政王这些年深居简出,朝堂之事尚且由心腹代劳,如今竟要亲赴灾地?有人暗自揣测,是为了收拢民心,还是另有隐情?
龙椅上的小皇帝正把玩着手里的玉如意,闻言抬起头,奶声奶气地问:“宛哥哥要走吗?带上朕好不好?”
晓流年:暗恋是带刺的救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