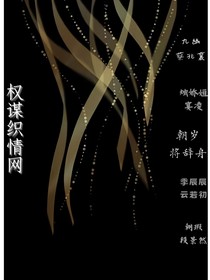花盛终零.上 (2-1)
阿筝院子里的木兰,第五年开得最疯。
枝桠窜得比墙头还高,粉白的花瓣堆了半院,连母亲晾晒的蓝布衫上都沾着细碎的花痕。阿筝坐在织布机前,手里的梭子穿得飞快,粗布上的纹路渐渐织出片新花样——不是甲胄的鳞纹,也不是战场的沟壑,是长戟的木柄缠上了木兰枝,枪尖挑着朵半开的花,倒像是把不肯生锈的温柔兵器。
“阿姊,今日镇上有集市,要不要去换些花种?”邻居家的小虎挎着竹篮站在院门口,他比去年又高了半头,眉眼间已见少年模样,只是看她的眼神还像当年那个扒着墙头的孩童,带着点怯生生的敬慕。
阿筝抬头时,一片花瓣落在她发间。“不去了,”她笑着拨掉花瓣,“这院子里的花够多了,再种怕是要把屋子淹了。”
小虎挠挠头,从篮子里掏出个纸包:“那我给你带了些新出的靛蓝,染布用的,比上次的鲜亮。”
纸包刚递过来,巷口突然传来马蹄声,嘚嘚的蹄音敲在青石板上,惊得院角的鸡飞起来。阿筝捏着纸包的手猛地收紧——这声音她太熟了,是驿站快马的调子,当年军帖送到村口时,也是这样急惶惶的响动。
三个穿皂衣的官差勒住马,为首的那个面生,手里捧着卷明黄的绢布,见了阿筝便扬声道:“前军卒阿筝接旨。”
阿筝的指尖瞬间冰凉。她放下梭子,拍了拍小虎的肩让他躲进屋里,自己走到院中央跪下,膝盖磕在落满花瓣的泥地上,软得像团棉絮。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前军卒阿筝,欺瞒入营虽赦,然女子执戟之事传扬民间,渐生靡靡之风,引得闺阁效仿,坏我朝纲常。更查及其兄阿烈,生前曾与敌国暗通书信,私泄军情,罪证确凿……”
后面的话像被风吹散的花瓣,碎得不成句。阿筝只觉得耳边嗡嗡响,眼前的木兰花瓣突然变成了雁门关的血,红得刺目。阿烈通敌?那个把最后半块干粮塞给她、自己啃了三天树皮的兄长?那个死在冲锋阵里、连尸骨都找不全的阿烈?
“不可能。”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磨过的戟柄,“我兄长战死于雁门关,忠烈祠里有他的牌位!”
官差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块碎裂的木牌,上面“阿烈”二字被劈得歪歪扭扭,边缘还沾着点黑褐色的痕迹,像是陈年的血。“忠烈祠?陛下已命人撤了他的牌位。至于你……”他的目光扫过阿筝的织布机,落在那匹织了一半的布上,“念你曾斩敌将,免你死罪,贬为营妓,三日内起程。”
“营妓”两个字砸下来,阿筝猛地抬头,看见官差腰间的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像极了当年敌将架在她脖颈上的那把。她忽然想起金銮殿上皇帝的眼神,那双盯着血木兰帕子的眼睛,深沉得像口古井,原来不是赞许,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朵带血的花连根拔起。
母亲从屋里扑出来,抱着官差的腿哭倒在地:“大人开恩!我儿是功臣啊!她斩过敌将的!”老太太的白发沾了泥,蓝布衫被扯得歪斜,露出肘间磨破的补丁——那是阿筝去年给她缝的,用的正是织了木兰纹的粗布。
官差一脚踹开她,母亲撞在木兰树干上,疼得蜷缩起来。阿筝扑过去抱住母亲,指尖摸到树皮上凹凸的纹路,那是她小时候刻下的身高记号,一道一道,像串没长大的年轮。
“我去。”她扶着母亲站起来,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河面,“但我要换身衣服。”
她走进屋里,从床底拖出个木箱。里面没有绫罗,只有那套洗得发白的铠甲,甲片上的血渍早已变成深褐色,像风干的木兰花瓣。她一件件往身上套,铜扣碰撞的脆响里,母亲的哭声隔着门板传进来,闷得像场下不透的雨。
最后戴上头盔时,她从镜里看见自己的脸。眼角的细纹深了些,耳后那片细腻的肌肤被晒得和脸颊一样黑,只有那双眼睛,还亮得像当年刚斩下敌将首级时,映着漫天烽火。
谁说女子不横戈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倾世双骄之冷少的掌心娇
- 陈国京都,繁华喧嚣。柳嫣,柳相府中不受宠的庶女,温婉灵秀,才情出众却隐忍内敛。冷逸尘,冷家大少,冷峻孤傲,手段狠辣,令人敬畏。一场花灯会,两......
- 7.8万字9个月前
- 师尊他阴魂不散
- 作者是新人,所以文笔可能不好,所以请见谅哈,我也会努力去改变。没什么可介绍的,所以就看吧,更新慢不要催啊,坐着也在赶稿ε٩(๑>₃&l......
- 0.4万字9个月前
- 救不了,放不下
- 谋权》中的大反派林归琛×小说作家许知安。我穿越了,一个我自己的小说我被抓了,被一个大反派我喜欢他,是一个大反派我不开心,大反派死了我救不了你......
- 2.0万字9个月前
- 医妃难囚改篇文
- 现代女医生苏瑶,在一次意外中穿越到古代,成为不受宠的王妃,卷入王府和宫廷的复杂纷争,初到古代的她,凭借现代医学知识,在王府中崭露头角,先是救......
- 1.5万字3个月前
- 权谋织情网
- 十几年前的一场案件将朝中的几位权贵联系在了一起
- 1.2万字3个月前
- 重登祂路
- 某个存在转世重修,一步步重登巅峰!
- 0.2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