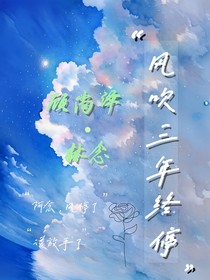槐香与旧契 (2-1)
处暑的风带着槐花香,漫过回春巷的青石板。苏晚蹲在布庄门口翻晒旧绣线,指尖触到团褪色的绛红丝线,线团里裹着片干枯的槐叶,叶脉的纹路竟和陈砚画的“回春巷图”里的槐树轮廓重合。
“这是十年前的线了,”她把线团拆开,槐叶碎成细小的绿渣,混在丝线里像撒了把碎翡翠,“那年你从国外寄来的颜料,我就用这线绣了幅槐花图,可惜没绣完就被念念扯坏了。”
陈砚正帮修鞋匠的徒弟画锥子纹样,闻言抬头笑了:“扯坏了才好,”他放下画笔,从画案下拖出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些零碎物件——有半块磨圆的墨锭,有枚生锈的顶针,还有张被雨水泡过的纸条,上面是他当年写的地址,字迹已经模糊,“这些都是当年没完成的事,现在倒成了接故事的扣。”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老物件修复档案”来了。他们给每个旧物件做了详细记录:顶针内侧的凹痕是补过多少件衣服的证明,墨锭的磨损程度能算出研过多少砚台,连那团绛红丝线,都用光谱仪测了成分,备注着“含槐花汁,光绪年间苏氏布庄常用染料”。“我们想办个‘未完待续’展,”年轻人指着档案册的空白页,“每个物件旁都留块布料,让参观者用自己的方式补完当年的遗憾:没绣完的槐花可以添朵新的,没写完的地址可以补个新的邮戳,把新旧故事缝成对儿。”
苏晚取来新染的绛红丝线,在展览用的素布上绣起槐花。针脚故意模仿十年前的手法,疏疏落落的,到了当年被扯坏的地方,突然换了细密的针法,像用新针脚轻轻裹住旧伤口。“补东西不能全盖了旧痕,”她穿线时说,“得让看的人知道,这故事走过弯路,才更金贵。”
陈砚在档案册的封面上画了串连环扣,每个扣都缠着不同的线:有的是棉线,有的是丝线,最末个扣上挂着片槐叶,叶尖的缺口和苏晚线团里的那片一模一样。“老物件就像这些扣,”他给扣描边时说,“看着散,其实都用故事串着呢,解开一个,就能拉出一串新的来。”
白露那天,展览在翻新的老布庄开幕。修鞋匠捧着那枚顶针,在素布上补了个小小的鞋样,针脚粗粝,和顶针的磨损痕迹正好呼应;补旗袍的老太太拿着半块墨锭,在空白处写了行小字:“当年没写完的情书,现在用墨香补”,字迹里还能看出年轻时的娟秀。
有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颤巍巍地走到那团绛红丝线旁。他从怀里掏出个褪色的荷包,荷包上的槐花只绣了一半,针脚和苏晚十年前的手法如出一辙。“这是当年给你娘做的,”他对苏晚说,“她总说‘等绣完这朵就嫁’,结果我走得急,没等她下针。”
苏晚的眼眶一下子热了,赶紧取来丝线,让老先生握着她的手,一起把荷包上的槐花补完。老先生的手抖得厉害,针脚歪歪扭扭的,却和苏晚的细密针脚缠在一起,像两棵老树的根在土里交握。
“这下圆满了,”老先生放下针时,眼角的皱纹里淌出泪来,“比当年想的还圆满。”
机器人工程师带着机械臂来了,这次没让机器模仿人手,而是给机械臂装了个小小的传感器,能识别旧物件上的岁月痕迹——摸到顶针的凹痕,就吐出粗线;触到墨锭的磨损,就换细线,绣出的纹样带着深浅不一的肌理,像把时光的纹路拓在了布上。“机器学不会遗憾,”他在旁边贴了张纸条,“但能记住遗憾的形状,也算种念想。”
念念背着自己的小绣绷,在展览的空白处绣了串小脚印,从老先生的荷包一直延伸到门口的槐树。“这是故事走的路,”她仰着脸对围观的人说,“以前的脚印浅,现在的深,以后我要让脚印一直走到槐树顶,让风把故事吹给更多人听。”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倘若南风知我意
- 两人的差距是许新意无法面对爱情软弱,尽管他面对林准安的直白和关心,他也无力做出选择。面对情场上的抉择他会怎么做呢?许新意从小就喜欢花,在长大......
- 0.2万字6个月前
- 爱人的失忆
- 1.1万字5个月前
- 风吹三年终停
- 有人在风中释怀,有人却在风中爱了又爱
- 0.8万字5个月前
- 余晖渐黯
- 洛瑶在碧海市小镇读书,成绩优异但性格孤僻,与同学保持距离,只有奶奶是她唯一的温暖。14岁就凭一手出神入化的黑客技巧,成为潜伏者黑客组织五大元......
- 5.0万字4个月前
- 如果可以回到那年夏天
- 二十二岁的向阳遇到了十六岁的沈栀,“我可以在这里工作吗,打杂什么的我都会,求你了”“我们这里不收童工。”…………“哥哥,我怕”“别怕,哥哥保......
- 0.9万字15小时前
- 人间方糖Luscious
- 书籍简介当圣彼得堡大学的东亚史学者白溪,带着她的论文与严谨闯入这座城市的风雪,赌场老板瓦西里的世界,从此有了不落幕的光。她是埋首文献堆的学术......
- 3.6万字14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