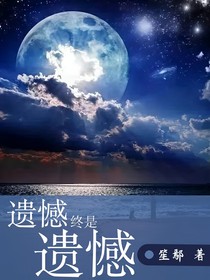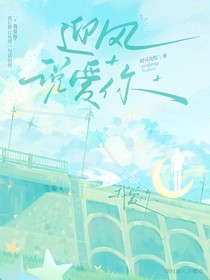归燕与新篇 (2-1)
谷雨的雨下得缠绵,回春巷的屋檐下多了几只燕子。苏晚抬头时,正看见只燕子衔着泥巴掠过晾衣绳,绳上挂着的靛蓝布被风掀起角,布上绣的水纹竟和燕子翅膀的弧度重合。
“它们回来了,”她把刚染好的柳绿色丝线收进竹篮,陈砚正对着张旧照片出神——是去年“城市记忆”长卷巡展时,在水乡廊桥拍下的画面,廊柱上挂着的长卷末端,新添了片绣着菱角的布。“你看这廊桥的影子,”陈砚指着照片,“像不像咱们布庄的门框?”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巡展日记来了。本子里贴满了各地的票根、手艺人的签名,还有张被雨水洇过的布片,是山里竹编师傅用竹篾压出的纹路。“长卷在南方遇到了黄梅天,”年轻人指着布片上的水痕,“有位老奶奶用桐油给长卷刷了层保护,说这样‘故事就不会被雨泡软’。”
苏晚取来防潮的桐油纸,裁成和日记本一样大的尺寸,用棉线缝了个封面,封面上绣了只衔着布片的燕子,布片上的纹路正是那片竹篾压出的痕迹。“雨能打湿纸,”她穿针时说,“但打不湿缝在里面的针脚。”
陈砚在日记的空白处画了串小小的地标:水乡的桥洞、山村的石碾、还有片刚抽芽的芦苇,芦苇的穗子用淡墨晕开,像苏晚绣过的蒲公英绒毛。“走得再远,”他给地标描边时说,“这些记号总能把长卷引回家。”
立夏那天,回春巷来了位特殊的客人——是巡展时在水乡遇到的绣娘,背着个沉甸甸的布包,里面是她给长卷新添的绣品:片用鱼线绣的荷叶,叶脉里裹着几粒真的莲子。“这莲子泡在水里能发芽,”绣娘把布包打开,“就像故事落在哪儿,哪儿就能长出新的念想。”
念念凑过去看荷叶,忽然指着莲子说:“我要把它们种在布庄的院子里,等长叶了,就绣片一模一样的贴在长卷上,让水乡的荷叶在这儿扎根。”她跑去找小铲子时,裙摆扫过陈砚的画案,带起张速写,上面是只停在绣绷上的燕子,翅膀的纹路和苏晚封面上的那只连成了线。
小满前后,长卷终于回来了。展开时,末尾的空白已经接了半米长:有山里孩子画的小竹屋,屋顶用金线绣了炊烟;有海边渔民缝的贝壳,壳边缘缀着细麻线,像海浪的波纹;最末处,是位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绣的半只燕子,针脚歪歪扭扭,旁边用拼音写着:“等它飞回北方的家”。
苏晚把那片鱼线绣的荷叶缝在回春巷石板路的尽头,陈砚则在荷叶旁画了道浅浅的水痕,一直延伸到布庄的门口,水痕里藏着小小的“砚晚居”风铃。“这就把南方的水引到咱这儿了,”他笑着说,“以后院子里的莲子发芽,就当是长卷捎来的礼物。”
布庄的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修鞋匠给长卷补了个新的鞋钉纹样,说要“给走远路的长卷加个耐磨的底”;机器人工程师带了台新的刺绣机械臂,这次竟能模仿苏晚的针脚弧度,在角落绣了朵小小的槐花,旁边注着:“学会的温柔,记在心里了”。
念念把种莲子的花盆摆在长卷旁,花盆上用彩线绣了串小脚印,从布庄门口一直到花盆边。“这是莲子长大的路,”她对围观的人说,“等它长出荷叶,我就带着它去南方,告诉那里的绣娘,北方也有会讲故事的荷叶了。”
入夏的蝉鸣响起时,陈砚在长卷的最新空白处画了道高高的弧线,像燕子掠过的轨迹。苏晚取来银线,沿着弧线绣了串小小的音符,每个音符里都裹着粒细沙——是年轻人从海边带回来的,说“让海风的声音也住进针脚里”。
檐下的燕子窝里多了几只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混着绣线穿过绸缎的轻响。苏晚坐在绣架前,给音符添最后几针银线,陈砚则在旁边整理巡展日记,忽然发现某页空白处,有片被燕子翅膀扫过的墨痕,形状竟像朵没绣完的蒲公英。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终末拯救计划
- “我们等待的太久了,希望这一次我们会成功,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法吉斯】”昏暗的房间中少女持棋落子,脚下是一张张照片,照片中的少女被墨水涂抹......
- 0.8万字6个月前
- 你好,我的顾先生!
- 0.4万字6个月前
- 遗憾终是遗憾
- 那年,他们都是八年级。他是个插班生,学习不错,她是班上的尖子生,还是班长。她与他成为了好朋友,两个人还一起报了美术班。她渐渐对他产生了情愫,......
- 1.4万字5个月前
- 余晖渐黯
- 洛瑶在碧海市小镇读书,成绩优异但性格孤僻,与同学保持距离,只有奶奶是她唯一的温暖。14岁就凭一手出神入化的黑客技巧,成为潜伏者黑客组织五大元......
- 5.0万字4个月前
- 薄荷糖现代校园文
- 0.4万字2周前
- 迎风说爱你
- 夏天治愈休闲文,夏天就该配着冰西瓜,冰棍,小狗,还有一大片的山和山泉水
- 6.8万字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