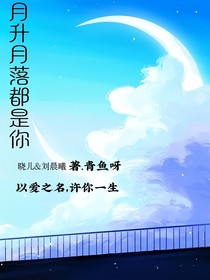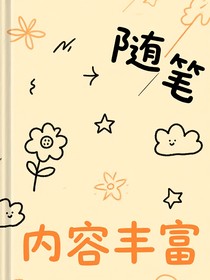蝉鸣与续章 (2-1)
夏至的蝉鸣刚起,布庄的竹帘就被晒得发烫。苏晚把新绣的“蝉纹扇”挂在门楣上,扇面用冰丝线绣了只振翅的蝉,翅膀薄得能透光,风一吹,倒像真有蝉鸣从丝线里钻出来。
“念念的暑期作业要编本‘手艺词典’,”陈砚帮着把晾干的蓝染布叠起来,布角的靛蓝色还在往下滴着水,“说要把修鞋的‘锥’、刺绣的‘绷’都画成插画,让城里的孩子认识这些老物件。”他拿起块染坏的布头,布头边缘的水痕像只蝉的轮廓,“你看这形状,倒能当词典的书签。”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手艺基因库”的方案来了。他们给老手艺人做了三维扫描,连苏晚绣绷上的木纹、陈砚画笔的磨损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再把这些细节转化成数据,储存在小小的芯片里。“我们想把芯片嵌在手工艺品里,”年轻人指着枚绣着银杏叶的胸针,“扫一下就能看到这枚胸针的绣法传承,就像给手艺办了张‘家谱’。”
苏晚取来细如发丝的金线,在芯片外套了层小小的布囊,布囊上绣了个迷你的“苏”字。“手艺得有个软乎乎的家,”她把布囊缝在胸针背面,“不然数据再全,也少了点人情味儿。”
陈砚在“手艺词典”的封面上画了串锁链,链环是各种老工具的形状:有的像绣针,有的像墨条,最末个环是只蝉,翅膀上的纹路和苏晚扇面上的蝉纹重合。“这些词看着生僻,”他给锁链描阴影时说,“其实都连着过日子的根,就像蝉鸣,每年夏天都来报到,听着就踏实。”
芒种那天,布庄成了“词典编辑部”。修鞋匠拿着锥子给孩子们演示“穿孔”,苏晚用不同的绣绷讲解“绷”的大小,陈砚则帮念念给插画上色——把“染”字涂成靛蓝色,“绣”字的偏旁用彩线描边,倒像字本身就带着颜色和纹路。
念念在“蝉”字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绣绷,绷上留着半只没绣完的蝉:“这是留给明年的,等我学会用金线了,就把翅膀补完。”她举着词典给来参观的人看,“您看这‘匠’字,多像个人弯着腰干活,旁边还得有只蝉陪着才不孤单。”
“手艺基因库”的首批作品展出时,蝉鸣正盛。有位戴眼镜的教授扫描了那枚银杏叶胸针,屏幕上立刻跳出苏晚太祖母绣银杏的照片,连针法里的小习惯都一模一样。“这哪是家谱,”教授推了推眼镜,“是把光阴都串起来了。”
机器人工程师也来了,他带来台能识别绣法的机器,却让机器跟着苏晚的动作学。机器绣出的蝉总差口气,他就在旁边贴了张纸条:“学不会的那点抖,是苏老师走神时想陈老师的样子吧?”
入伏后,布庄的院子里种了片薄荷。苏晚摘了叶子泡水,给编词典的孩子们解暑,陈砚则在每张词典的内页角落,都画了片小小的薄荷叶。“翻书的时候闻到味儿,”他笑着说,“就像夏天在布庄院子里待着一样。”
暴雨来的那天,他们正在给“手艺基因库”的芯片做防水处理。苏晚用蜡线把布囊缝得更严实,陈砚则在芯片的数据里加了段蝉鸣录音。“万一芯片受潮了,”他调试着播放器,“至少还能听声夏天的响儿。”
雨停后,夕阳把布庄的影子拉得很长。苏晚发现晾在绳上的蓝染布被风吹得碰在一起,布料摩擦的声音竟和蝉鸣合上了拍。陈砚赶紧取来录音笔,把这声音录了下来,说要加到“手艺词典”的“声”字条目里。
“你听,”他把录音笔递给苏晚,“老布和蝉都在说,日子就得这么热热闹闹地缠在一起。”
念念抱着刚编好的词典睡着了,词典摊开在“续”字那页,页脚被她不小心滴了滴薄荷水,水痕像只正在爬的小虫子。苏晚轻轻合上书,发现陈砚在“续”字旁边写了行小字:“故事像蝉蜕,旧的留下,新的接着长。”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唯忆琳
- 本书主要写两对主人公:瑶梦姩与琳婠婠谭小枣与夏染星故事剧情:瑶梦姩在爱人,死后的半年后,成为了神咒怨首领。谭小枣在长达六年的霸凌下,终于等来......
- 2.3万字7个月前
- 月升月落都是你
- 苦命的设计师姐姐x外冷内热的总裁弟弟
- 0.3万字5个月前
- 囚金之影
- 小时候仰头望天,总觉得穹顶之下皆是坦途,白云游过的地方都能抵达。可后来才明白,随着年岁增长,天空不过是越扩越空的幕布,而脚下的路却像被命运的......
- 10.2万字2周前
- 推舟
- A城秋和中学高级教师林谒在两年前得了脑肿瘤,肿瘤压迫大脑记忆神经中枢,切除后留下了轻度的认知障碍。他的同事兼竞争对手韩讳竟然试图帮助他调整认......
- 0.6万字2周前
- 开联:暗夜降临
- 暗夜降临时,星星球,你们完了!不是吗?
- 1.0万字1周前
- 随笔内容丰富
- 有双男、双女,但双女主偏多一点
- 2.3万字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