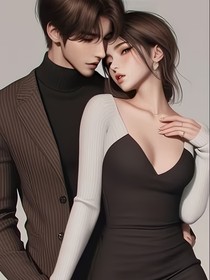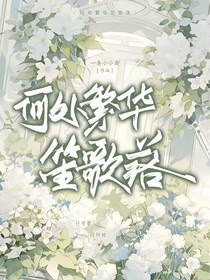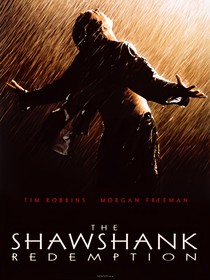秋实与藏珍 (2-1)
秋分的阳光带着点清冽,布庄院子里的晒秋架支了起来。苏晚把染好的秋叶色丝线晾在架上,从浅黄到赭红,像把秋天的颜色裁成了条条丝带。陈砚蹲在旁边翻晒去年的墨锭,墨香混着桂花香飘过来,倒让空气里多了层温润的底色。
“市档案馆的人来了,”苏晚捡起片被风吹落的银杏叶,叶纹像天然的绣稿,“说要收些老物件做永久馆藏,让咱们选几件有故事的。”她指着樟木箱里的旧绣绷,“这个是我娘年轻时用的,边角都磨圆了。”
陈砚从画案下拖出个木匣子,里面是本翻得卷边的绣谱,夹着几张泛黄的便签,上面是他出国前写的纹样草稿——有次苏晚说想绣组“四季果”,他就把见过的枇杷、杨梅、柿子都画了下来,旁边注着“用金线勾果蒂更亮”。
“这些便签算吗?”他把便签摊开,阳光透过银杏叶的缝隙落在纸上,草稿里的果子像被镀了层金边,“当年总怕忘了你说的话,记了满满一本。”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来了扫描仪,要给老物件做数字档案。他们给旧绣绷拍了360度照片,连木头纹理里的细小划痕都录了进去;扫描绣谱时,发现某页空白处有个浅浅的指印,是苏晚当年蘸着浆糊翻页时留下的,倒成了意外的印记。
“我们想做个‘记忆盲盒’,”年轻人指着档案系统的界面,“每个数字档案都配个实体小物件,比如绣绷的木片、绣谱的纸样,装在盒子里让大家抽。抽到的人可以根据线索,来布庄找对应的老物件,听它的故事。”
苏晚选了些碎布头,都是历年绣坏的边角料,有牡丹的花瓣尖、蝴蝶的翅膀根,她把这些碎布缝成小小的锦囊,每个锦囊里塞张写着故事的纸条。“就像拆礼物,”她把锦囊串成串挂在晒秋架上,“老手艺的故事,总得带点布的温软。”
陈砚则在每个数字档案的封面画了个小符号:旧绣绷旁画了只停驻的蝉,绣谱边添了片银杏叶,连那盒便签的封面,都画了颗半红的柿子,和苏晚当年绣坏的那个果脯纹样重合。“符号认起来快,”他解释道,“就像老街上的幌子,老远一看就知道是哪家。”
档案馆来取物件那天,布庄里飘着新收的桂花。苏晚把娘的旧绣绷擦得发亮,绷上还留着最后一次使用的针脚,是段没绣完的兰草;陈砚把便签按时间顺序排好,最末页夹着片当年的银杏叶,叶脉已经脆得像薄纸。
“这些不止是物件,”馆长摸着绣绷的木棱说,“是能摸得着的光阴。”他让人给布庄颁了块“城市记忆守护点”的牌子,牌子是用老槐树的木料做的,苏晚在边缘绣了圈缠枝纹,把“守护”两个字轻轻裹在里面。
念念把自己绣的第一个完整荷包也放进了捐赠箱。荷包上的兔子歪歪扭扭,耳朵还绣反了,她在旁边贴了张画:兔子背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绣线和画笔。“让它替我陪着老物件,”她说,“等我学会了更厉害的手艺,再来看它。”
霜降那天,数字档案上线了。有人抽到了苏晚娘的绣绷锦囊,根据线索找到布庄时,手里捧着个同样磨圆了边角的竹编筐:“这是我奶奶编的,当年总用它装绣活,说跟布庄的绣绷是老相识。”
苏晚把两个老物件摆在一起拍照,竹筐的纹路和绣绷的木棱在阳光下交错,像两道并行的时光轨迹。陈砚在照片旁题了行字:“老物件认亲,比人还准。”
夜里收东西时,苏晚发现晒秋架上还挂着个锦囊没被取走,里面的碎布是片没绣完的蒲公英。她把锦囊打开,月光落在纸条上,是她当年写的:“风会带种子去远方,但根总在这儿。”
陈砚正把新收的银杏叶夹进今年的绣谱,闻言抬头笑了:“那就留着它当念想。”他往砚台里加了点清水,研墨的声音混着窗外的虫鸣,“老手艺的根,扎在这儿呢,不怕风刮。”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豪门虐恋之现代版凤求凰
- 季婉,季家温婉的小姐。她与残疾的向凛少爷签契约恋爱,婚后她悄然掌控局面。向凛逐渐爱上她,然而前女友回归引发误会,季婉离开。向凛追悔,开启追妻......
- 8.5万字6个月前
- 何处响笙歌
- 任笙歌与段何处的故事始于校园的一次偶然邂逅。段何处如一阵不羁的风,围绕在清冷的任笙歌身旁。随着相处渐深,情愫暗生。但段何处家庭突遭变故,他被......
- 3.1万字6个月前
- 无缘轨道
- 时间不会让人忘记。产生遗忘的是释怀。
- 3.3万字5个月前
- 安颜夏梦
- 因家中破产,魏老爷子不得不将魏家孙女送去联姻,而联姻对象居然不是夜家小少爷,而是夜家千金!
- 1.8万字5个月前
- 不是吧,这就破防了?
- 路迢迢,女,芳龄十八,貌美如花,偶然得知自己只是一本甜宠文里的恶毒女N号后彻底破防,思考了三秒后,她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 0.9万字5个月前
- 尼古丁的救赎(科幻版)
- 尼古丁的救赎
- 1.1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