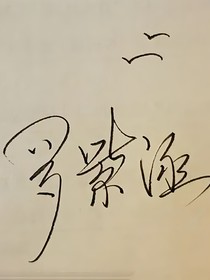时光里的传承 (2-1)
念念三岁那年,已经能踩着小板凳,扒在绣架边看苏晚做事了。她不吵不闹,小手捏着根没用的线头,跟着母亲的动作一上一下,嘴里还咿咿呀呀地念叨:“针要走直线,像爸爸画的线一样。”
陈砚正在旁边画新一季的绣稿,闻言笑着抬头,笔尖在纸上点出个小小的圆点:“念念说得对,针脚歪了,绣出来的花就站不稳啦。”他把画好的桃花图推到女儿面前,“你看这花瓣,要像妈妈叠的纸船一样,有弧度才好看。”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忽然抓起支毛笔,蘸了点清水在宣纸上乱涂。苏晚刚要阻止,陈砚已按住她的手:“让她画,说不定能画出朵不一样的桃花。”果然,念念的“画作”歪歪扭扭,倒像极了枝头初绽的花苞,带着股野趣。
苏晚后来真把这“稚拙桃花”绣在了个布包上,摆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有客人问起,她就笑着说:“是我女儿画的,比她爸爸画的多几分孩子气呢。”
那年秋天,市里办非遗市集,苏晚带着学生们去摆摊。陈砚特意画了套“四季绣稿”,让大家现场演示——春日绣柳,夏日绣荷,秋日绣菊,冬日绣梅。念念穿着小肚兜,上面是苏晚绣的小老虎,在摊位间跑来跑去,手里举着片枫叶,非要往苏晚的绣绷上贴:“妈妈,给枫叶绣件金边的衣服。”
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蹲下来看念念玩,忽然说:“我在国外学过服装设计,一直想把传统刺绣融进去,可总找不到感觉。看您绣的枫叶,忽然明白该怎么下手了。”他指着苏晚正在绣的叶脉,“这针脚不是简单的线条,是有呼吸的。”
苏晚递给他一本绣谱:“其实刺绣和设计一样,都要懂‘留白’。就像陈砚画画,从不把纸填满,总要留些地方让看画的人自己想。”
年轻人拿着绣谱翻了半晌,忽然抬头:“我能跟您学吗?我想做些年轻人喜欢的绣品,让更多人知道,这老手艺能穿在身上,也能活在当下。”
陈砚正好送画过来,听见这话笑了:“我们正想办个进阶班,教大家把刺绣用到现代服饰上。你来得正好,给我们讲讲国外的设计理念,也算互相学艺。”
市集结束时,夕阳把摊位的影子拉得很长。念念趴在陈砚肩头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片没绣完的枫叶。苏晚收拾东西时,发现年轻人留下个笔记本,里面画满了设计图,有牛仔外套上绣着缠枝莲,有帆布鞋上缀着小绣片,每一张旁边都写着:“从针脚里找自由。”
冬天第一场雪落时,进阶班开课了。年轻人带来几个同学,有学插画的,有做首饰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怎么让绣品更“年轻”。有人提议用荧光绣线,有人想把绣片做成手机壳,吵吵嚷嚷间,陈砚忽然说:“其实不用刻意求新,就像晚晚绣枫叶,用老针法,绣现代人的心事,就够了。”
他拿出幅新画,画的是布庄的窗景:苏晚坐在绣架前,念念趴在她腿上看绣线,窗台上的茉莉落了层薄雪。“你们看,”他指着画里的光影,“老房子,旧手艺,新生命,放在一起就很好。”
苏晚忽然想起什么,从柜子里翻出个旧木箱。里面是母亲年轻时的绣品——有给婴儿做的虎头鞋,有陪嫁的被面,还有块没绣完的手帕,上面的兰花只绣了半朵。“这是我妈当年怀我的时候绣的,”她摸着泛黄的缎面,“后来忙得没时间,就一直搁着。”
“我们把它绣完吧,”陈砚拿起那帕子,“让念念也学着绣两针,也算三代人的针脚聚在一起了。”
那天下午,布庄里格外安静。母亲坐在旁边看,苏晚绣花瓣,陈砚补叶脉,念念捏着最细的绣针,在角落歪歪扭扭地绣了个小太阳。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帕子上,把三代人的影子叠在一起,像幅慢慢晕开的水墨画。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凭谁解花语
- 解雨臣×原创女主第一次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多担待等写的差不多,会根据这个文整理一个更好的文,感谢
- 3.8万字6个月前
- 甜恋常
- 如果这都不算恋爱的话,那什么算恋爱呢?
- 0.6万字5个月前
- 恶毒宿主先走一步
- 1.0万字5个月前
- 下一个转折点
- 她是无人问津的小职员,却在夏日风中揭开豪门新篇章。
- 2.0万字4个月前
- 复仇之影:柔弱表象下的暗潮涌动
- 李婉柔的姐姐李婉清因不堪校园霸凌而自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李婉柔的世界彻底崩塌。为了给姐姐报仇,她决定伪装自己,假装成一个柔弱无助的女孩,悄......
- 1.4万字3天前
- 我的散文小说
- 关于季夜寒和江容的故事,并于一些散文
- 1.3万字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