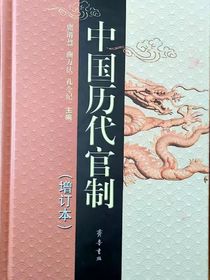二十 (3-2)
原本以为会如往常一样,看到房门被敲响,或者那人直接走进房间。然而,房门依然静静地敞开着,那人却踌躇良久,未能踏入。此时,我内心涌动着无法抑制的情绪,一种冲动与不安交织在一起,对愿望未能如期实现的忐忑心情愈发强烈。每一秒流逝都像是对我全身造成了隐约的震颤,使得情况越发扑朔迷离,令我无所适从——我在发疯似地犹豫与撕裂,究竟是否应该出声询问?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故?为何他今夜选择等待我们打破沉默?他曾以一贯的态度展现出对沉默的赞赏,而此刻的坚韧不拔又要求我们如何应对?在尊严与想法的交织中,我们需要作出怎样的反应?我的身躯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手掌发麻,眼睛和皮肤也感到异常灼热。
母亲这时再次转向我,期待从我低垂着的黑暗眼神之中寻找某种鼓励或暗示。然而,由于未能洞察我内心的真正意图,她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门上的把手。此刻的她仿佛流露出了曾经让祖父为之震撼的冷酷目光,紧紧盯着把手,脸色苍白。尽管我和祖父都保持沉默,她内心的焦虑却愈发明显。我身在安乐椅上,即使试图紧紧咬紧牙关保持平静,却始终感到自己那紧擦着那排洁白如玉的细牙的上唇翘起在痛苦的痉挛中:自己有意无视与忽略了整整一个月,原以为在面对随后的分别会波澜不惊,然而当真正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内心悲剧时,现实的残酷远超我内心的微弱挣扎。最终我所有的力量似乎都在这一刻消散无踪。而此时,门板再次传来了敲门声——仅仅两下,急促而微弱。我终于从苍白无力的双唇间吐出了几个字,喃喃细语地出声:“…他就要离开了。”我的声音那么低,显得完完全全地绝望了。这一举动使母亲瞬间下定决心,不再犹豫,清晰地传达了自己的意愿,成功阻止上尉完成敲门后的离去:“等等,先生。是的:请进——上尉先生。”至于为何母亲要加“先生”一词以称呼对方的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为了强调邀请的是友非敌,抑或是出于一种无言的默契,我们都知道门外之人的身份。然而具体缘由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从始至终也都一刻不歇地心生邀请:请进,西蒙。
他进来了,一身戎装,左手提着狹岝而纲长的行李箱。
接下来是一段冗长的沉默,宛如死寂的深海,寂静到令人感受到压抑的窒息感。墙枳上的时钟时针滴答作响,秒针不断前进,然而周围依然一片寂静。祖父手中的烟斗微微颤抖,升腾起丝丝缕缕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模糊了客厅中每个人的视线。经过漫长的等待,绿色眼睛的主人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带着湿润的沙哑,仿佛白雾与黑暗交织在一起,映衬出他眼鼻上方淡淡的忧伤泪沟。他用低沉的法语缓缓说道:“我要走了。”
母亲听到这句话后,双手不禁紧握,她低下头,几乎呈一种不正常的僵直角度,以至于脊背显得异常突出。光线也因此变得灰暗,投射在她和旁边的祖父身上。祖父用力抿着干巴巴的嘴唇,皱纹更加明显。即便隔着烟雾,也能看到他口中闪烁的晶莹泪光,湿润而黏腻。
德国上尉的话语中透露出他内心的波澜。他嘴唇从始至终都非常红润,像浸透了水一般地对我们三人说道:“我请求重返战斗师,终于得到了这个恩典。今夜我将奉命启程,目的地可能是俄国的前线。”他继续说道,目光似乎落在我们三人坐在壁炉前的身影上。他的喉结艰难地滑动,语调虽然平淡而淡然,却难以掩盖其中的颤抖和沙哑。“我们的军队取得了伟大胜利,”他继续说着,话语如同一缕朦胧的雾霾,仿佛是从烟斗中飘散出来的:“但那边气温零下四十度,我们的士兵难以承受。”
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屈服,这是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他们无一例外地逆来顺受,即便是这位个体也不例外——此刻的我,面色苍白如纸,即便在火光的映照下亦无法掩盖。我的双唇犹如乳白色玻璃瓷花瓶的边缘般微微开启,勾勒出一种类似希腊雕像中悲怆的嘴角。我亦能感觉到,我的额头与发丝交界处,汗珠不是缓缓渗出,而是如泉涌般喷溅而出。
沉默的呼号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大明风云录
- 嘿,朋友!你想知道明朝那些事儿吗?你想了解明朝那些著名官吏的传奇故事吗?打开这本书,你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明朝那个充满魅力的时代。他们的故事......
- 4.8万字4个月前
- 秦始皇大战吕布
- 奇幻的穿越故事
- 0.1万字4个月前
- 中国历代官制
- 由鹿谞慧、曲万法、孔令纪主编的这本《中国历代官制(增订本)》总共分为十章内容,全面地介绍了从先秦到民国历朝历代的官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机......
- 3.2万字4个月前
- 新世界:革命与旧秩序
- 新的世界,到底是为革命而战,还是为旧秩序而死,骰子已经掷下,接下来我们只能前进!
- 0.3万字4个月前
- 无限流:瓷爹穿越记
- 『无限流+ch+all瓷+微搞笑』瓷爹的穿越琐记点点收藏吧宝宝们
- 新书4个月前
- 关于高一政治的一些重难点
- 高一,初高中链接用,里面解答了一些困扰初中几年政治术语难懂的问题。
- 0.1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