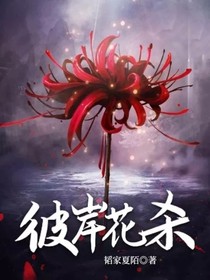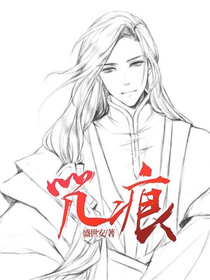希曼诺夫斯基之心(下) (10-2)
尼采,在哲学研究之余,创作了大量模仿舒曼风格(注:他最出名的作品是〈梦幻曲〉)的音乐作品,狂热拥抱瓦格纳(注:代表作是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之后,又向瓦格纳剧烈倒戈,以同样的激情顶礼赞颂比才(注:法国作曲家,代表作〈卡门〉)与肖邦(注:代表作是21首夜曲,被誉为‘钢琴诗人’)。尼采早年创作的降B大调玛祖卡,近乎是肖邦《降B大调玛祖卡(Op. 7 No.1)》的抄袭之作,尽管前者以二拍子为节奏,但其旋律的发展与后者并无二致。
尼采着迷于肖邦音乐,在肖邦狂想曲中感到一种奔放而自由的激情,尼采认为这在德国艺术中是难得见到的珍品。尼采一向以波兰贵族自称,对肖邦有亲切感。 尼采以波兰贵族自居,也是批德国人的狭隘性的一种表达。肖邦认为舒曼音乐不像音乐,过于片段化,这个是错误的评价,舒曼是典型的德奥音乐的正统,尼采虽然也批舒曼,但舒曼一直是尼采的心中音乐的高贵类型的代表,其意义超过了舒伯特,舒伯特由于在贝多芬强大的阴影中,没有舒曼音乐的明显的自我风格。在肖邦音乐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点斯拉夫民族的精细和敏感。
那瓦格纳呢?1883年2月13日瓦格纳去世。“死讯让尼采实实在在地躺在了病床上,他既伤感又高兴。”一方面,他心中燃烧起无限的与瓦格纳决裂以来所感到的个体情感上的失落;另一方面,他心底也生出一股从瓦格纳处得到解放的快感,对尼采来说是他通向真正自我的决定性步伐。这是决裂了。但是之前呢?1868年10月27日的音乐会上,瓦格纳名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和《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让他持续八年的膜拜之心再次高涨。尼采在早期寄希望于德意志精神的再生,他将瓦格纳的音乐看作振兴德意志精神的希望。尼采指出,德国音乐,首先是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是一个强劲而光辉的发展历程。尼采将瓦格纳作为巴赫、亨德尔、贝多芬、莫扎特等德奥古典音乐的传人。
可是为什么决裂呢?
关于“什么是德意志精神?”这个问题,尼采与瓦格纳发生过一场争执。当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共同的,即超越和消解民族性。他们对民族性的思考达到了形而上的层面而不是政治性的思考。他们追求超越民族的东西,追求包罗万象的普世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精神,而德意志民族的优点就在于广泛吸纳其他民族优点。但,在这一观点的具体的处理上,尼采比瓦格纳更尖锐与极端,他直指当时的德国人走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而瓦格纳的超越民族性有部分个人因素,由于他的混血身份,他和当时的德国人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说他更加接近于法国人的特质,体现的更多是欧洲人身上的特性。但是瓦格纳本人却是希望自己获得“德意志性”,也就是被德国人所接受的。因此当瓦格纳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重新被德国文化接受时,尼采十分反感,他认为瓦格纳偏离了自己的天性,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够“瓦格纳”的。尼采对于瓦格纳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于当代性的批判,就是对于当代社会的批判。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最重要的批判性著作、出版于1888年9月底的《瓦格纳事件》尝试的就是一种对当代心灵的诊断,核心是一种颓废分析。“颓废”一词自波德莱尔之后被赋予了正面含义,即在这种生命力的虚弱之中,才会产生一种更高的艺术的灵感。因此,尼采把瓦格纳称为颓废艺术家时,其实兼具有正面意义的。“因为谁如果想要克服颓废,就必须要经历颓废,”所以他对瓦格纳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迈出颓废之后的那一步的批判。
现在呢,现在,战争爆发,起因似乎是一场政变。内忧外患啊内忧外患。外界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思潮传入波兰,我的好友密钦斯基是“青年波兰”运动的代表人物,可是,我早年崇拜肖邦和早期斯克里亚宾(注:神秘主义作曲家,最出名的作品是〈狂喜之诗〉,早年创作肖邦式的音乐)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我并不想抛弃掉他们传统的充满典雅旋律的浪漫主义……可是,累累战火就撂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身前炸响。
哇伊拉之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凹凸:金的妹妹是团宠
- 给金私设了一个妹妹叫春是团宠。一些人可能会ooc请见谅,小尬剧
- 4.8万字5个月前
- 彼岸花杀
- 一位女杀手,因为救一朝好心,救了一个老婆婆,得到了血泪,引来杀身之祸。死后与自己留在玄武大陆的灵魂合二为一……(作者我是一个追星女孩,偶尔会......
- 15.7万字5个月前
- 咒痕
- 故事内容简介:蓖虚国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皇子啻吻,但也是被诅咒之人。对于所有人来说,杀掉被诅咒的人,才是最稳妥的选择,一个又一个监视者来到了皇子......
- 31.2万字5个月前
- 奇妙萌可之捕捉花朵森林的萌可-d637
- 讲述了乐美,乐可,珍珠捕捉15只花朵萌可
- 0.4万字5个月前
- 葫芦娃之二娃失忆了?
- 二娃和六娃在一起
- 0.1万字5个月前
- 虽隔岸,亦欢喜
- 更新至53章:甜似蜜!
- 9.2万字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