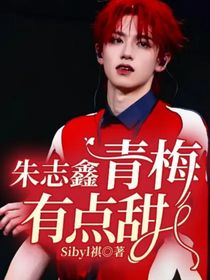彩虹出现那天 (3-2)
这是他去陇西那年,她赠他的临别礼物。当年为了报答李信“眉头挨刀”之恩,她悉心拣选耐穿耐磨的布料,亲手为他缝制了这件衣裳。虽然当时已考虑到他会长个子,尺寸尽量往大了做了,可毕竟过去这么久了,这衣裳早就不合身了吧?
天哪,他竟然还留着!
冬儿只觉一种感动从内心升起,满满堵住了咽喉。
幸好随身带着针线,她坐下来,把旧衣上的破口、毛边又缝补了一遍。
手起针落,一针一线,仿佛在把那个人的影子从她淡去的记忆里慢慢补回来。
一场罕见的暴雨猝不及防地袭击了咸阳城,强烈的对流风夹着雨如鞭子抽打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很快,除了雨中行驶不多的马车,整个咸阳仿佛成了一座空城。
那日她正好出宫替夫人采买邯郸的糕饼,回宫途中暴雨肆虐,她乘坐马车路过北街石巷时,巷子深处出现了一抹深黑浓重的色彩,定睛看去竟是一个少年孤零零地跪在石板路中,任冷雨浇击身子,硬是一动不动。
他看起来与政儿年纪相仿。是谁家少年?甚是可怜啊!
冬儿心软,当即让马夫停车,拿起一把油布伞朝那少年走去。
她把伞伸过去,为少年挡住头顶的雨,关切询问道:“敢问是谁家公子?怎的大雨天跪在此处?”
他抬起头,仿佛被雨水糊住了视线,他努力眨眨眼,苍白的脸上浮起一种复杂的表情,仿佛诧异、又仿佛困窘。
人生之初见,他狼狈得犹如一匹受伤的孤狼,她将雨伞倾斜向他。
他冷冷侧过了脸:“李夫之子,李信。”
她恍然惊悟,这竟是大王和政儿的救命恩人之子!她下意识地几乎把整只伞都靠了过去,为他挡雨,自己大半边身子全湿了。
她顺着李信面对的方向看去,眼前是一座朴素的宅邸,牌匾上刻着李字。这少公子为何跪在自己家门口?她问了几次,他却不答,无奈之下她只好召来同行的宫人,让他们回宫把政儿带来。
李夫将军刚牺牲不久,她总不能眼看恩人之子这般惨状而一走了之。
他不吭声,她只好默默站在他身边。大雨越发滂沱,弥漫的白色水汽将整个世界笼罩在朦胧之中。他们就这样一跪一站,方寸的油布伞下,如同一片小天地,与这雨雾彻底隔绝。
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武将之后,他面庞精悍、身正体直,眼睛里有某种困兽般坚决不屈的神情,全身散发出剑一样锋利的气息,竟有些令人凛然生畏。
他似乎在坚持着什么、抵抗着什么?她心想。
他头也不抬,忽地冰冷飘来一句:“你走吧,不要多管闲事。”
唉,真是不识好人心。
任他冷言驱赶,她不理会,反正谁也管不着谁。
两人就这么在雨中僵持了半个时辰,直到政儿赶来,当今太子驾临,李信这才只好说了实情。
李将军战死后,李夫人厌惧了武将的人生,“练了武功,成了武将,生死就由不得自己了。”,她不希望儿子重蹈父亲的覆辙,一定要他弃武从文,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而李信于这狂风暴雨中跪在家门外,只为向母亲宣示他坚定的从戎之志。
“大丈夫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不以个人安危为至高。武将者,外应征战沙场、开疆拓土,内则守望相助、保家安民。从戎报国乃先父之愿,亦是李信之志,无可更改。”
当年才十来岁的李信,是以多远的志向在铺垫未来的道路、以多大的勇气在坚持自己的选择,大概只有与他意志相当的政儿可以看清。
政儿赞他“男儿铁石志”,决然陪他一起立于雨中。终于,李府那扇沉重的大门开启,李信赢得了母亲的谅解与支持。
雨过天晴,彩虹横跨在消散的乌云之上。李信脸上的迷蒙散去,他睁开纯粹浓黑的眼睛,透过灿烂的阳光微笑了,那是一个少年期冀未来的模样,熠熠闪光、耀眼夺目。
大秦赋:启信逢冬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绝世:小霍娘今天又在努力不被撅
- {原创}霍雨灵在六岁觉醒武魂时,意外获得了魅魔体质,得知自己以后要被从史莱克学院撅到星斗大森林,此时,纯洁小白花系统找上门,小霍娘开始了努力......
- 4.6万字3个月前
- 朱志鑫青梅有点甜
- 【已签约,时间线混乱,不定时更新,会员,金币加更】钓系帅哥朱志鑫×开朗沙雕宋今禾有个特别会撩的竹马是种什么体验丑话说在前头,不爱看左上角退出......
- 6.8万字3个月前
- 斩神:命运如期而至
- 命运之神从来不会心软一切的开始是何时,以为的开始真的是开始吗…王面“无论你是谁,你在哪,你都是我的枝枝。”林安祉“愿这次得偿所愿。”王面×林......
- 11.3万字3个月前
- 终极一家:无药可医
- 细水长流的爱情,先家国后个人,日久生情向,暗恋向。❤️【灸舞×苏苏(原创)】:“我爱苍生,也爱一人。”❤️【灸舞】:“有些病,无药可愈;有些......
- 51.0万字3个月前
- 奇文:赎
- “我远比你想象的更爱你”
- 4.0万字3个月前
- all鑫:ABO疯人楼
- 【Nova文社/1V6/病态文学/无尽的黑暗/ABO文】“阿程,我们真的好爱好爱你啊!”传说疯人院是低级o/共享o/劣质o的地方,在这里,只......
- 1.0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