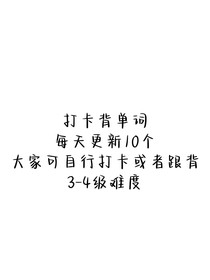—— (4-4)
《鬼吹灯》和《盗墓笔记》更接近美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对神话的描述,墓葬制造者,是神话英雄,奇珍异宝,是隐喻承载者,而不论探险者还是野心家,都是走遍大地的说书人,他们的冒险,更像是入场券,他们的争斗,更像是一唱一和,为的是给讴歌提供合理的节奏。这两部书,不是斤斤计较的现实主义,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盗墓》
《盗墓笔记》,是用墓葬为线索,重述中华文明史。
——《盗墓》
制服衬人提人,不仅仅是因为制服本身的特点,而是因为它的样式统一,模糊了单个人的特征,却也进行了人性集中,似乎穿上一身衣服就可以集中很多人的品质,让所有穿过这类制服者的事迹堆加在一个人身上。
——《硬汉》
这正是娱乐圈的残忍之处,聚光灯下的人,在没有画像佑护的情况下,等待被涂污而后抛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求他在投身欲望深海的同时,竭力维持自己的干净纯白,这种要求,隐蔽而又明目张胆,善良而又残酷,像是看走钢丝绳表演,希望走绳的人不要掉下来,完全忘了,我们的围观,就是让他走上去的动力。
——《挂相》
岛屿,总是似近还远,似幻还真,虽然和我们只隔着一片海、一种语言,但却由此成了一个异域,它的小、封闭、孤独,非但没有成为它的缺陷,反而让它成为一个摇篮,更容易培育情绪,也更容易打理,更容易成为一个完美世界。
——《岛屿》
人的灵魂、人格,起初只是一粒沙粒,我们负责往上包裹珍珠质,使之圆润光洁,一旦人生衰退停滞,那些珍珠质难免会剥落,让最初的沙粒显形。决定珍珠形状的,是最初的那个沙粒,决定人生退潮期形貌的,还是最初的那个沙粒。那个沙粒,叫自我。
——《寄托在李安身上的那个理想》
面对高晓松,面对我们时代的一切艺术家,一切曾经滋养过我们的人,我们都挣扎在这种困惑里,我们被内心的那个他打动,却被皮囊上的那个他滋扰,一边按照内心的标准进行评价,一边按照皮囊的标准表示厌恶。
——《皮囊》
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只好羞辱自己的需求,判断力没有合适的应用对象,我们就开始羞辱自己的判断力,羞辱它的依然存在,羞辱它的耿耿于怀,用各种反智的方式。任何时代,无用武之地的那些玩意,必然遭遇羞辱,正义得不到声张,我们必然羞辱正义,希望总是绝灭,我们肯定矮化希望,爱情没有下落,我们必然乐于用征婚节目来羞辱爱情。羞辱自己的本质需求,是在周围环境不肯配合时的必然反应。
——《罗玉凤神话》
生命形态的复杂,只能说明环境的坚硬复杂,过多的生存技能,只提示出生存的不易。
——《阴柔不是一种罪过》
值得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统一定调的男性气概,而是生命形态的简单,是每个人顺应内心,长成自己该有的样子,而且不会被人横加干涉。
——《阴柔不是一种罪过》
网络时代,虽然貌似给了人更大的自由,那自由却捆绑着陷阱,因为,自由的真正含义是,别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自身的自由于是被淹没了,被别人的自由限制了。
——《没有个性的人》
藏书文案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穿越:我在各种小说当恶女
- 简介见第一章,总而言之就是疯批恶女纯爽文,有感情线但是暗线,基本算没有
- 0.0万字4个月前
- 寇杰小杂文
- 0.2万字4个月前
- 一起打卡背英语单词(3——4级难度版)
- 每天打卡背十个单词一起打卡背适合成人本科学位考试以及四级难度一起背
- 0.4万字4个月前
- 宿命之海
- (虐)如果这是循环,那为什么这次死的不是他
- 2.7万字4个月前
- 暮色玫瑰(叙旧著)
- “祈舟,世界上没有蓝色玫瑰,花是假的,你的爱也是假的。”暮回红着眼对眼前的人说。暮回三年前丢下这句话便出国了,三年后,他重回云海,一款新品种......
- 0.3万字4个月前
- 适合即可
- 江焫,阎麋一对冥冥之中注定的恋人,可最后还是没有挨住现实,二人不知最后…无固定主角,无光环,挺现实夜粒,潘望江仪,小叶总夜柠,小野黎途…更多......
- 2.6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