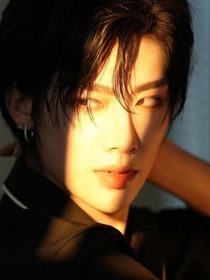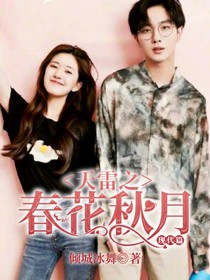信 (2-1)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见字如面。
写下这封信的时候大头在收拾包,训练馆里的灯光刚熄灭一半,球拍袋拉链摩擦的声音在空荡的场地上荡出轻响。忽然想起每次比赛结束谢场时,看台上亮成星海的灯牌和横幅,那些被呐喊声裹着的名字——"莎莎""大头",总让我们觉得,身后站着一整个宇宙。
还记得第一次搭档混双时,我俩在球台两侧站得笔直,教练在旁边笑说"像两棵没长开的小白杨"。那时候我总嫌大头发球不够转,他总吐槽我扑正手时像只横冲直撞的小豹子。练到后来,球台成了最懂我们的朋友:知道我接发球时喜欢先抿一下嘴,知道大头侧身攻前会悄悄调整握拍的力度,知道我们俩眼神一对,就明白下一拍该往哪里跑。
这些年在赛场上跑过的路,大概能绕地球好几圈。巴黎奥运会混双决赛那天,最后一个球落地时,场馆里的欢呼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可我们俩盯着球网看了好几秒,都没说出话。后来有人问,站在领奖台上是什么感觉?其实记不清太多细节了,只记得国歌响起时,手心里全是汗,握着奖牌的手指在微微发颤——那不是紧张,是觉得,原来这么多人的期待,真的能变成沉甸甸的力量。
也有过难捱的日子。输掉关键比赛的晚上,我会抱着球拍坐在更衣室里发呆,大头会绕着训练馆一圈圈散步,直到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有次混双输了半决赛,回去的大巴上,窗外的路灯一格格往后退,我忽然说:"你说,我们是不是还不够好?"大头没接话,只是把包里的巧克力塞给她——那是每次赢球后,球迷总会往包里塞的那种。
但第二天一早,球馆的门总会准时被推开。擦汗的毛巾拧出的水迹,球鞋在地板上磨出的声响,捡球机嗡嗡的转动声,把所有的沮丧都泡进汗水里。因为我们知道,看台上有那么多双眼睛,不仅在看我们赢球时的雀跃,也在看我们摔了跤之后,怎么咬着牙爬起来。
有个画面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去年全锦赛决赛,最后一分落地时,全场的"莎头加油"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我转身时差点被地上的线绊倒,大头伸手扶了一把,俩人对着笑出了眼泪。那时候忽然懂了,混双最妙的地方,从来不是"我"赢了,而是"我们"没输。就像球台两侧的两个人,不管谁跑得更快、打得更狠,最终都是为了让中间的球网,见证我们最默契的样子。
巴黎我们走出来了,北京的天气很好,常和你们说的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怎么就没听进去呢
常常在后台收到球迷的信,信封上画着歪歪扭扭的球拍,里面夹着晒干的花瓣,或者写着"我把考试考了第一名,就像你们拿了冠军一样开心"。每次拆开这些信,都觉得像是握住了无数双温暖的手。其实我们也会在训练间隙偷偷刷手机,看大家剪辑的比赛视频,读那些带着感叹号的鼓励,甚至会为了"莎莎今天的发球角度是不是又刁钻了"这类讨论笑出声。
有人说运动员的人生是被计时器切割的,可因为有你们,每个数字都变得有了温度。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混双决赛那天是我的生日,看台上忽然响起生日歌,全场的手机闪光灯跟着节奏摇晃,那一刻觉得,全世界的温柔都落在了球台上方。还有大头的生日,收到过球迷手工织的围巾,针脚歪歪扭扭的,却比任何名牌都珍贵——后来冬天训练,总偷偷围着它去器材室。
这些年,我们看着看台上的面孔慢慢熟悉,有些阿姨从我们十几岁看到现在,鬓角添了白发;有些学生球迷举着"考完试就来看你们"的牌子,从校服换成了学士服。你们总说我们是光,其实你们才是追光的人,用千万点微光,照亮了我们跑向球台的路。
最近训练馆新换了记分牌,电子屏亮起来的时候特别晃眼。有次练到深夜,我盯着上面的"0:0"出神,忽然说:"你看,不管赢过多少球,下一场开始,永远都是零。"大头点点头,把球抛起来发了个侧旋——就像十年前第一次搭档时那样,球在空中划出的弧线,又轻又坚定。
我们永不认输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毒蛇帮or西西里里家族?
- 纯娱乐
- 1.3万字1年前
- stubborn
- 讲述了韩国女子团体persephone忙内Yulia(沈媛琦)与zerobaseone成员Ricky(沈泉锐)的双向奔赴会有虐,但不多
- 1.0万字1年前
- 都颠了,颠点好啊
- 主角是一名道士,而如的朋友们也是个个身手不凡,有的是杀手,有的是特工,而有一些则是不知
- 2.5万字1年前
- 可恶的臭弟弟
- 烟草清冷御姐VS变态病娇奶狗。一个有天赋,一个有实力。谁才会更胜一筹?
- 0.1万字1年前
- 苏新皓:娃娃亲
- 三代苏新皓×四代林子菁,值得看,甜文,全程无虐,做梦素材,故事大致内容:苏新皓一见钟情了一个女孩,与她订了娃娃亲,却被李飞看上,成为四代,获......
- 3.3万字1年前
- 天雷之春花秋月现代篇
- 这是继春花秋月续写后,关于春花回到现在寻找回秋月再续前缘!本小说纯属虚构,是同人影视,禁止转载,抄袭!(小说里面的图片、明星头像来均来源于网......
- 11.2万字1年前